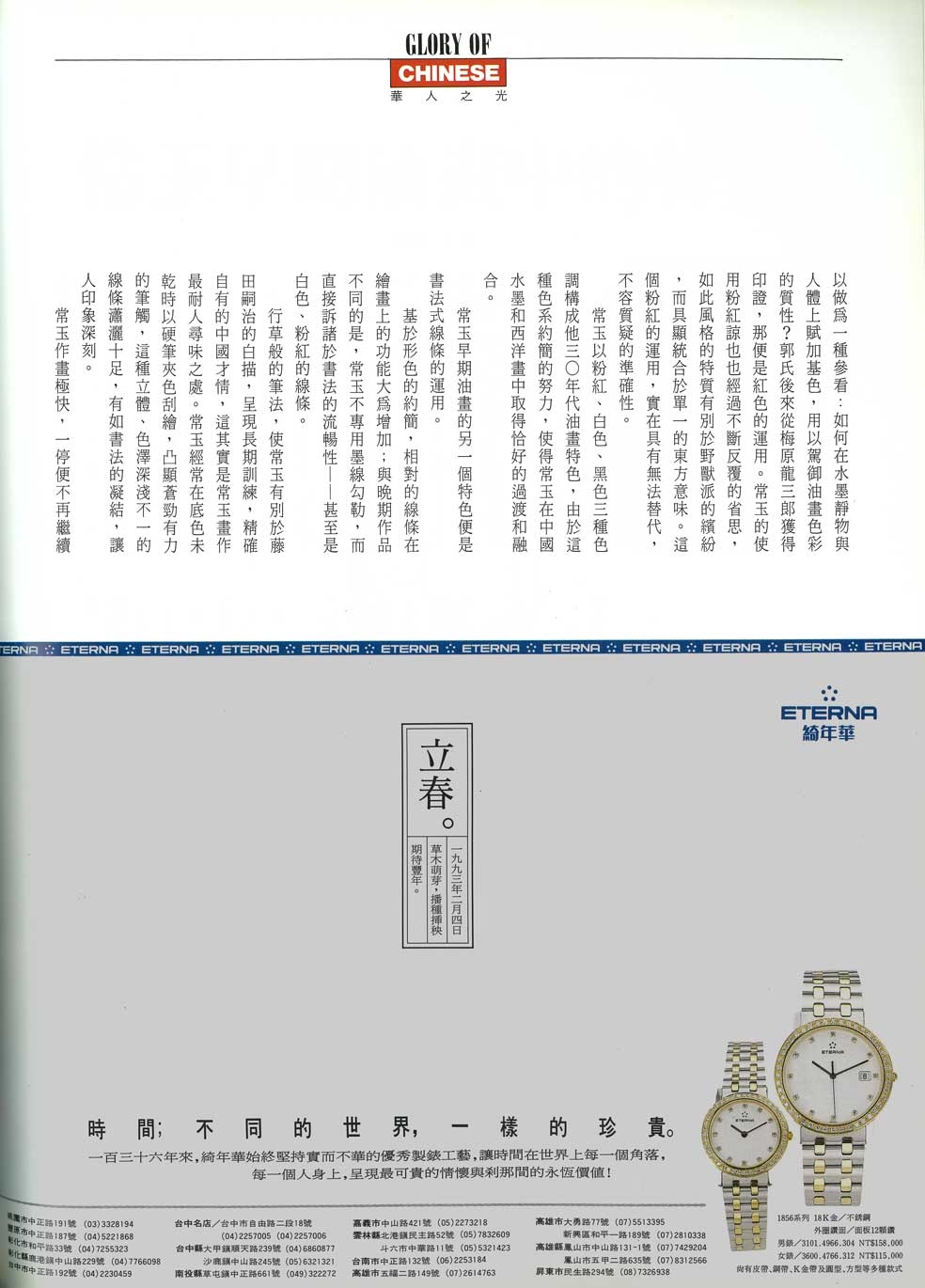常玉於一九二〇年到達巴黎,先前已有林風眠、徐悲鴻來法,三人與次年抵歐的潘玉良日後廣為人論,以為中國早期西歐習藝的代表;近期修史,大體不出此四人範圍。
由於天命境遇使然,這四人的歸屬各異。徐悲鴻、林風眠回國後分掌中央大學藝術系及杭州藝專,對近代美育影響深遠;尤其徐悲鴻所倡的寫實風格,至今盛而不衰,奠定他在美術史上巨擘的地位。然而徐氏專斷排新的保守作為,對中國現代藝術的發展究竟有所助益或阻礙,則另有議論。
潘玉良於一九二八年始回國任教,抗戰時再返巴黎,終老異鄉;算來對近代中國美育,頗具參與事實。相較之下,常玉流落在外,至一九六六年意外去世為止,與故國一生睽違,可說是對中國美術界的延展毫無關連。
今天我們重讀歷史,若以藝術成就與創作天份而論,這個比較的秩序恐怕是要倒過來看的。常玉毫無疑問才華橫溢,非其他人所能企及。徐悲鴻創作力之弱,已是公論。英國評論家克拉克(John Clark)在「中國畫中的一些現代化問題」(一九八六)一文中說:「徐悲鴻和吳作人只是二流畫家,但卻形成了一個足以影響全中國的繪畫王朝」,所言甚是。(註)主要是困於才情和觀念偏狹的緣故。徐氏在三〇年代晚期大肆抨擊馬諦斯及其他現代畫派,獨尊十九世紀學院寫實繪畫為圭臬,自是容易阻絕耳目。
常玉的發展之所以不同,乃是來歐之後有別於他人的習藝觀念。徐悲鴻、林風眠、潘玉良皆進美術學院習畫,常玉則感於當時藝壇蓬勃而逕自投入,薰染了旺盛的創作氣息。彼時馬諦斯(年紀長常玉四十四歲)在歐洲藝壇已是卓然有成,畢卡索、盧奧、布拉克、梵.東根亦相當活躍,常玉側身其中,亟於思齊的意圖是可想而知的。今日看來,常玉可說來到巴黎創作,而非單一的讀書習藝而已。
常玉很快的結合了蒙帕拿斯(Montparnasse)地區的巴黎畫派,發揮己長,掌握了當時歐洲對東方藝術注目的時代脈息,在法國的畫壇打出了名氣。除了先後入選「獨立沙龍」(Salon des Independants)和「替樂麗沙龍」(Salon de Tulerie)外,一九三〇年還列名GRUND出版社印行的「當代藝術家字典」。
二十世紀初歐洲畫壇對東方藝術甚為尊重。馬諦斯、高更從不諱言自東方美學形式中獲得靈感;而巴黎畫派中梵谷、莫迪里亞尼亦是如此。日本畫家藤田嗣治更以流暢密合、一筆究竟的人體線畫技驚一時。這對聰穎過人的常玉自是啟示良多,想在歐洲出人頭地,唯有表現特有的東方才賦不可;關於這點,常玉終生奉行不二。
常玉早年畫作多為靜物和裸女,前者受吳昌碩的影響,後者則廣為當時畫壇所普及,例如馬諦斯、亨利.摩爾便是。
常玉早期油畫的特色之一是形色的約簡。以這個角度便可測知他與馬諦斯相異之處,後人單純的將常玉的畫風歸結於馬諦斯的影響,有失於武斷。常玉在沙坑街畫室中曾與友人談及努力於簡化的過程,足見他對形式自始至終的篤定。常玉早期的油畫勿寧說更接近於表現主義的風格。
為了追求約簡,常玉不在繪畫中做太多的描述,而務期以最少的形色發揮最大的功能,由這點看來,常玉是極富現代創作意識的,而這恰恰亦與中國文人畫的精神相符;一種接近極限的表現思維。
反映繪畫顏色上,常玉早期作品也顯示出簡約慎密的考量。他刻意在黑白基調中加添顏色——一種極淡、彩度極低的粉紅。一九五〇年代郭柏川在宣紙上表達中國式油畫的嘗試可以做為一種參看:如何在水墨靜物與人體上賦加基色,用以駕御油畫色彩的質性?郭氏後來從梅原龍三郎獲得印證,那便是紅色的運用。常玉的使用粉紅諒必也經過不斷反覆的省思,如此風格的特質有別於野獸派的繽紛,而具顯統合於單一的東方意味。這個粉紅的運用,實在具有無法替代,不容質疑的準確性。
常玉以粉紅、白色、黑色三種色調構成他三〇年代油畫的特色,由於這種色系約簡的努力,使得常玉在中國水墨和西洋畫中取得恰好的過渡和融合。
常玉早期油畫的另一個特色便是書法式線條的運用。
基於形色的約簡,相對的線條在繪畫上的功能大為增加;與晚期作品不同的是,常玉不專用墨線勾勒,而直接訴諸於書法的流暢性——甚至是白色、粉紅的線條。
行草般的筆法,使常玉有別於藤田嗣治的白描,呈現長期訓練,精確自有的中國才情,這其實是常玉畫作最耐人尋味之處。常玉經常在底色未乾時以硬筆夾色刮繪,凸顯蒼勁有力的筆觸,這種立體、色澤深淺不一的線條瀟灑十足,有如書法的凝結,讓人印象深刻。
常玉作畫極快,一停便不再繼續;與其說是個性,不如說因襲於書法創作使然。有人說常玉作畫的誠動不夠,實在是一知半解。
常玉表現早期油畫的另一個特色便是「以白定物」的創作理念。常玉深得傳統水墨留白的奧義,並且能夠進一施用於西洋繪畫中「量體」和「空間」等的問題之上。常玉對於白色的使用,幾乎是無所不能,或為物體,或為虛空,甚或線條;隨心定賦,表現大膽自由的創意。
他的白色看似平常,其實肌理層次處理得極好,配合約簡至極的構圖看來靈氣生動,傳達了豐富的中國意象。
常玉早期的油畫文人氣息深厚,相較於晚年的民俗風格甚有不同,這其中環境的變遷、個人的遇合、材料的差異均有影響。前述作品中的特色,日後皆有替改,然而一路相續演進是毫無疑問的。
逾越半世紀後的今日,我們再看常玉的畫作,不禁深感於他創作上無礙自得的天份,常玉在當代中國藝術上的成就,應是再無異論了。
註:參閱臺北市立美術館出版「早期旅法畫家回顧展專輯,中國-巴黎」中,進入國際藝術的大熔爐——中國畫家及巴黎畫派(一九二〇~一九五〇)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