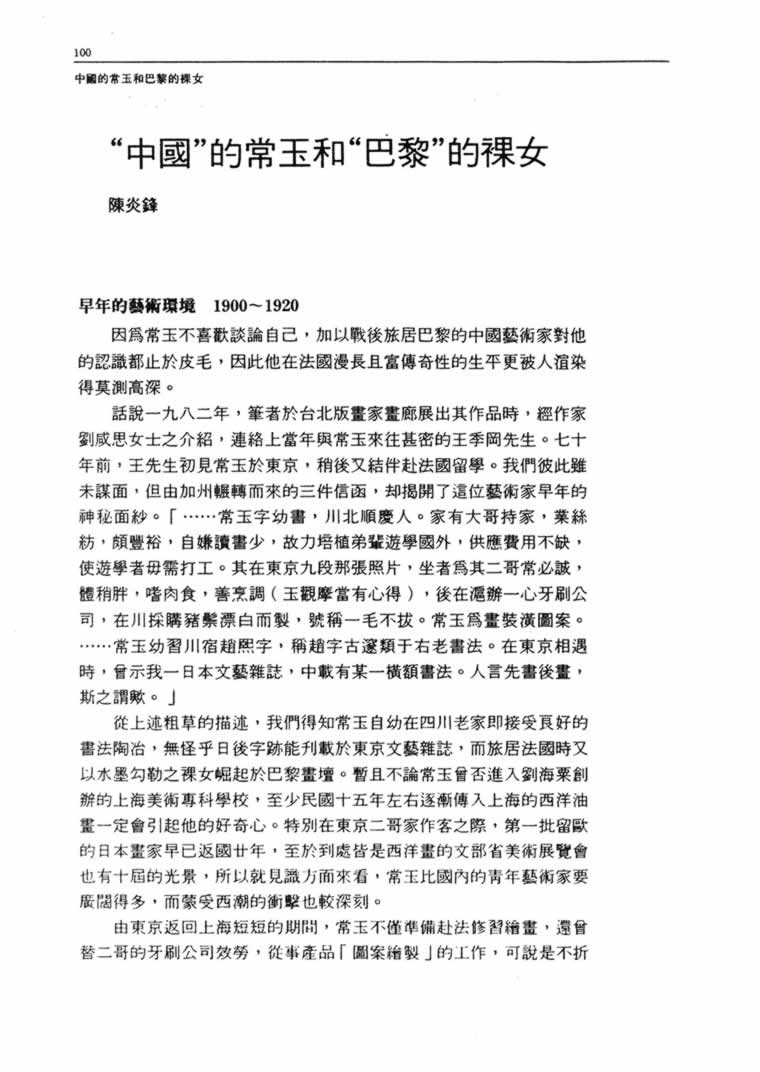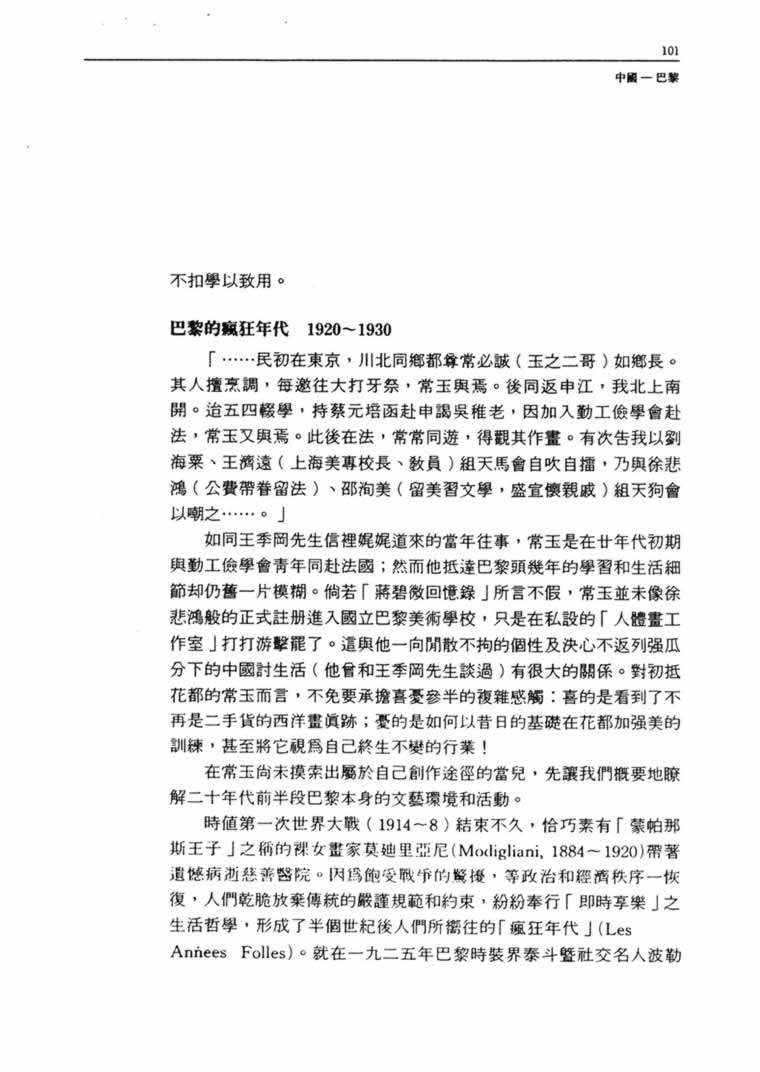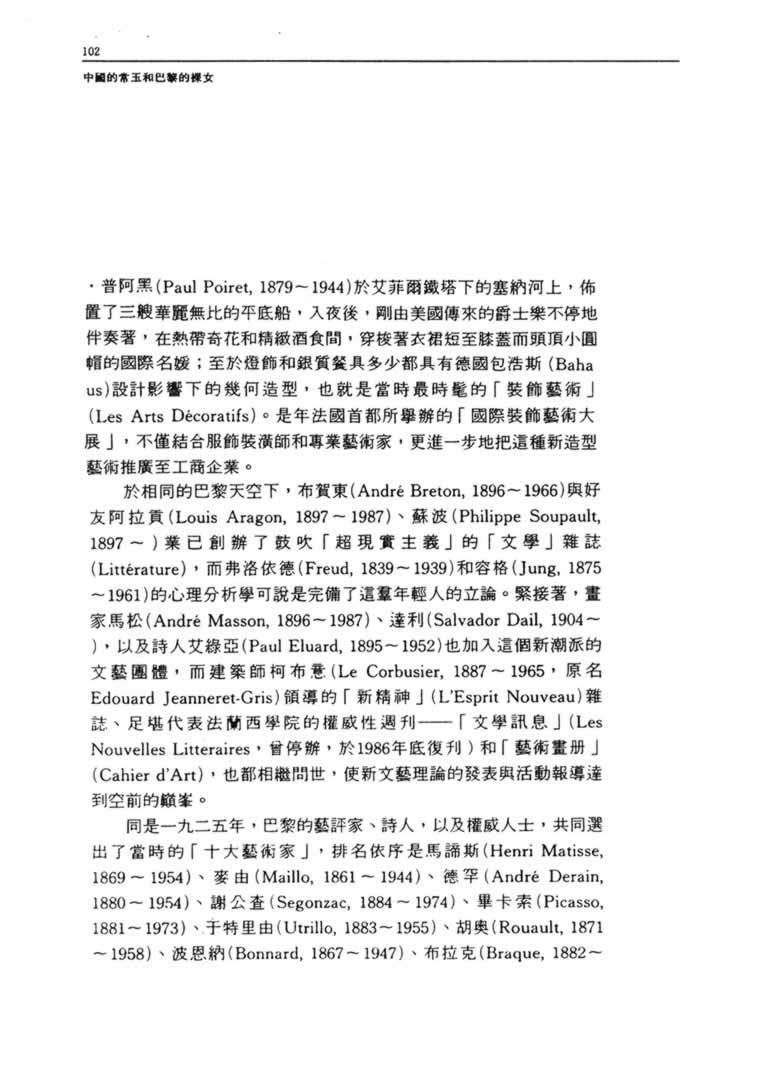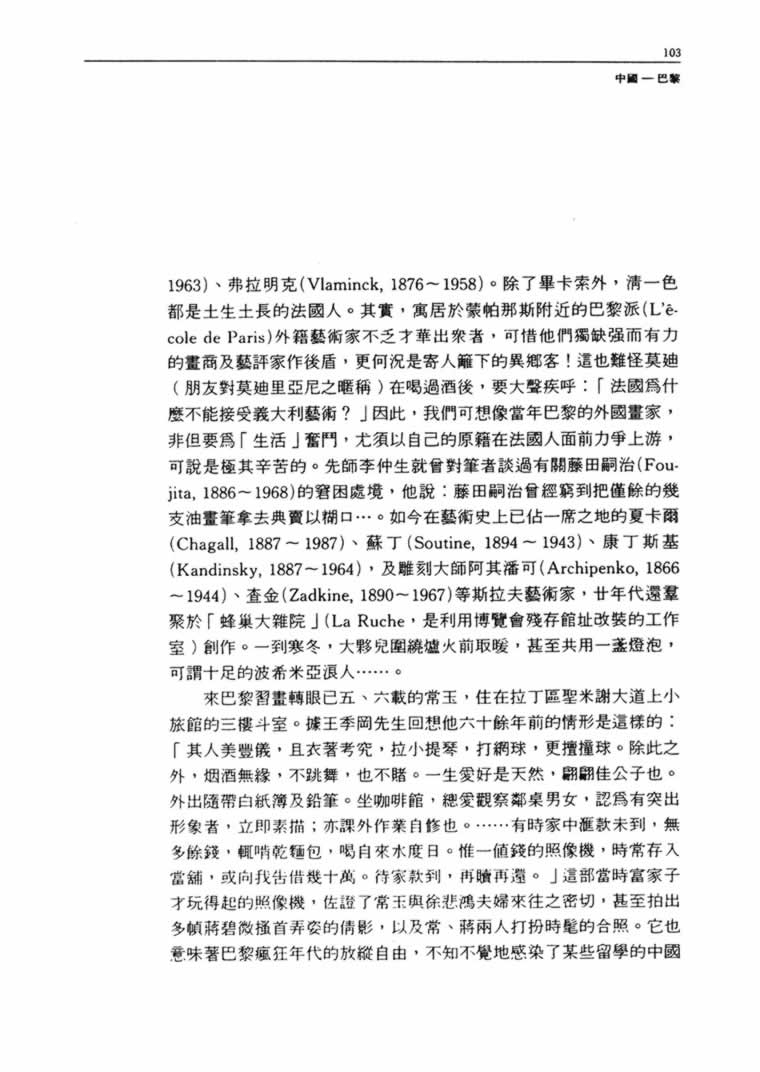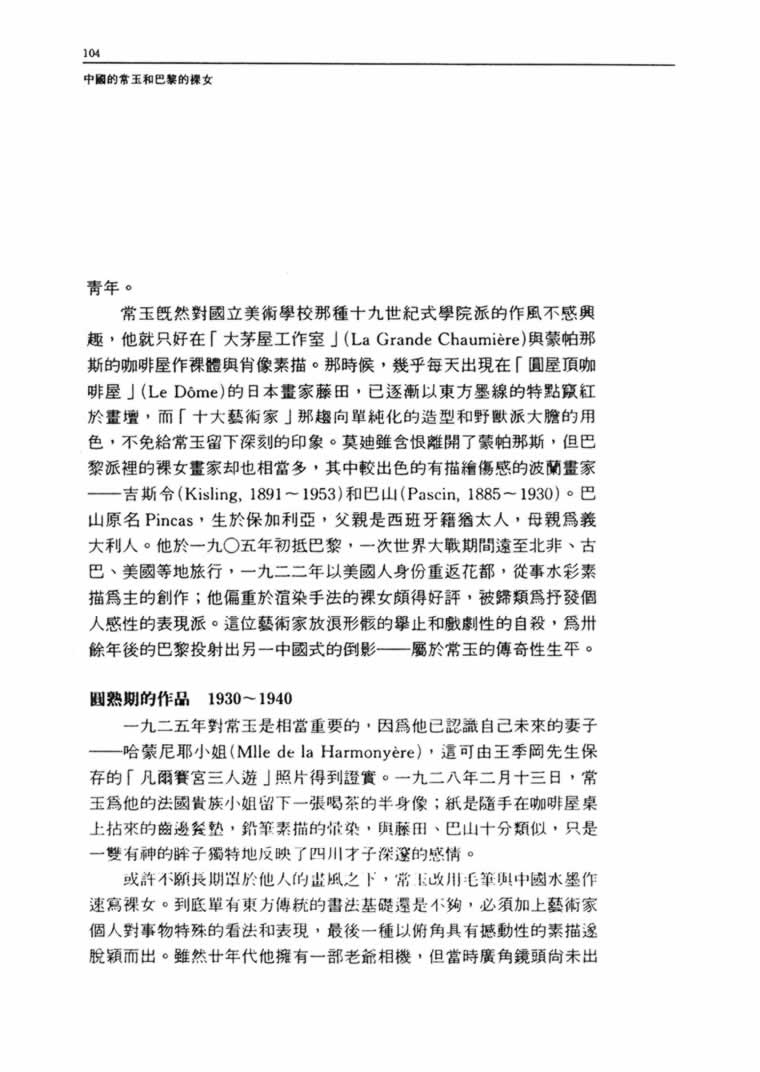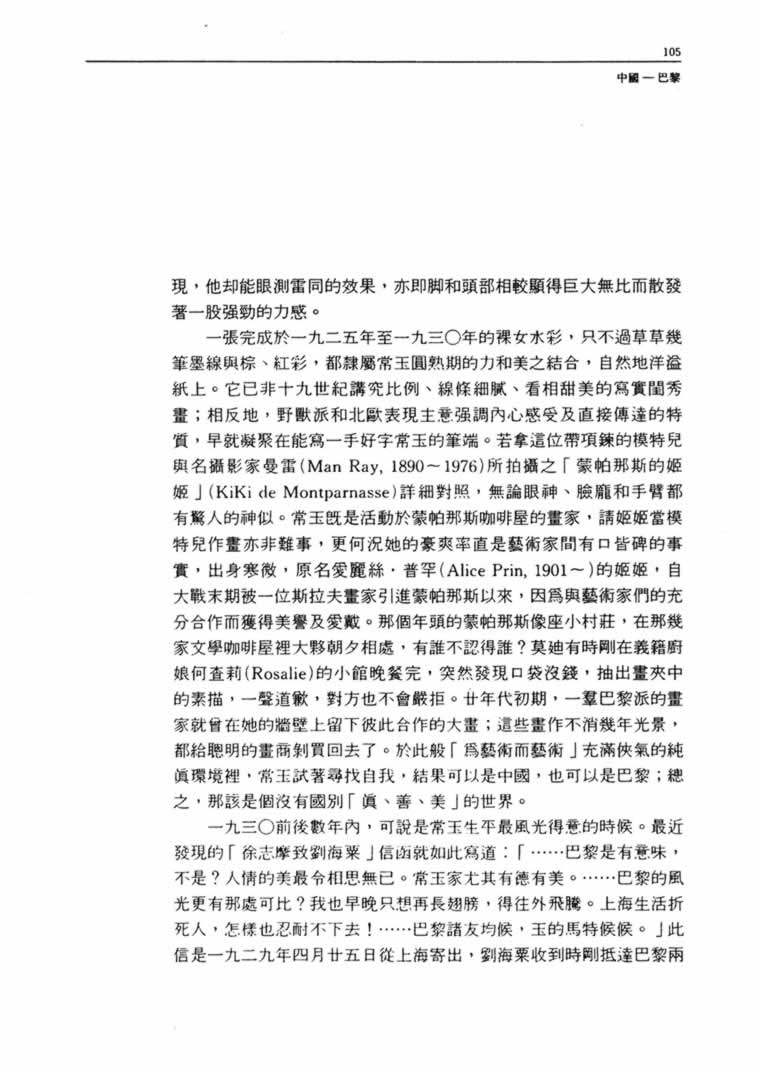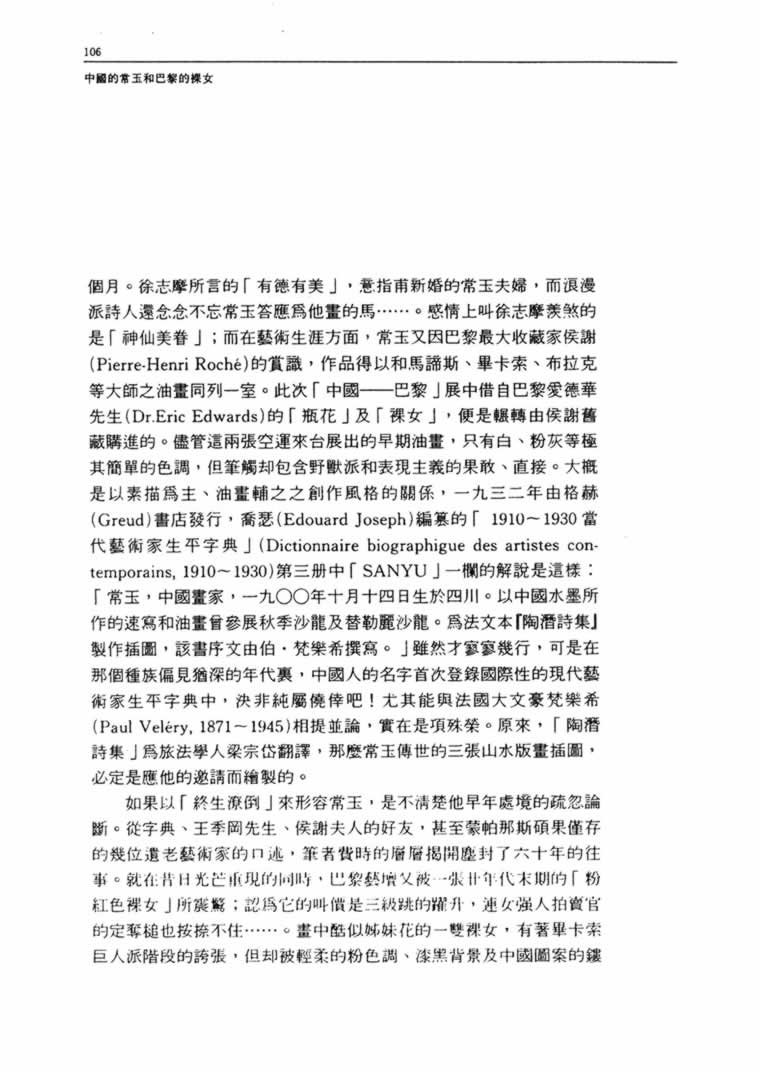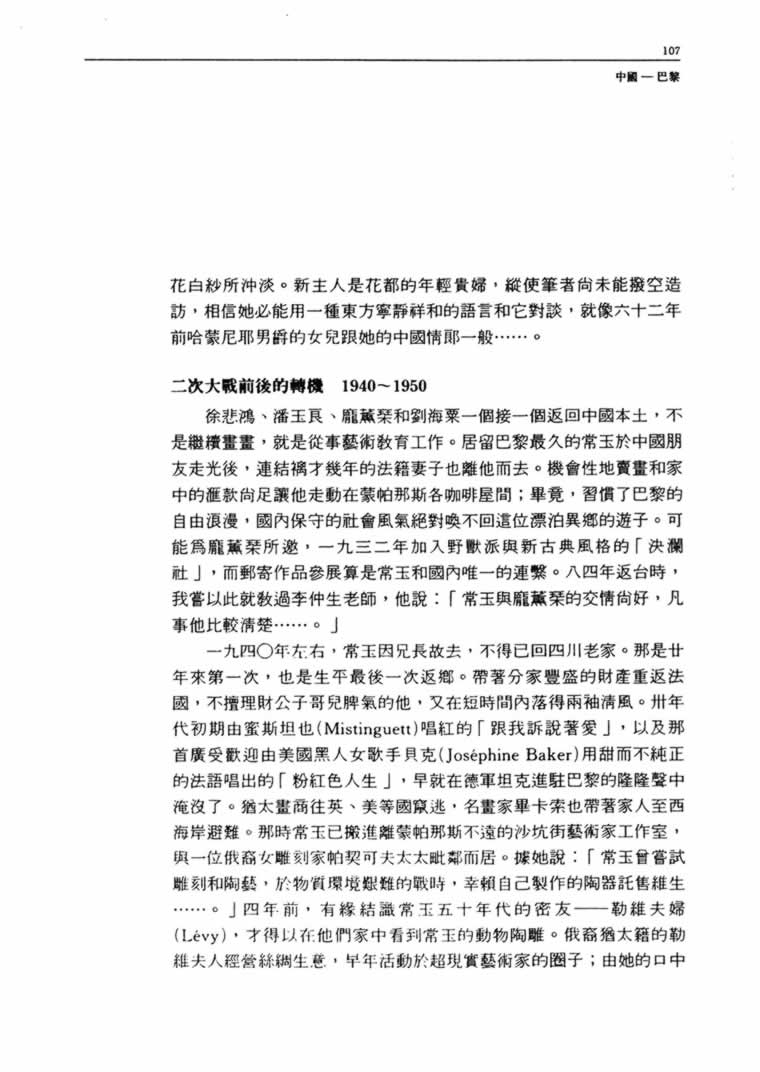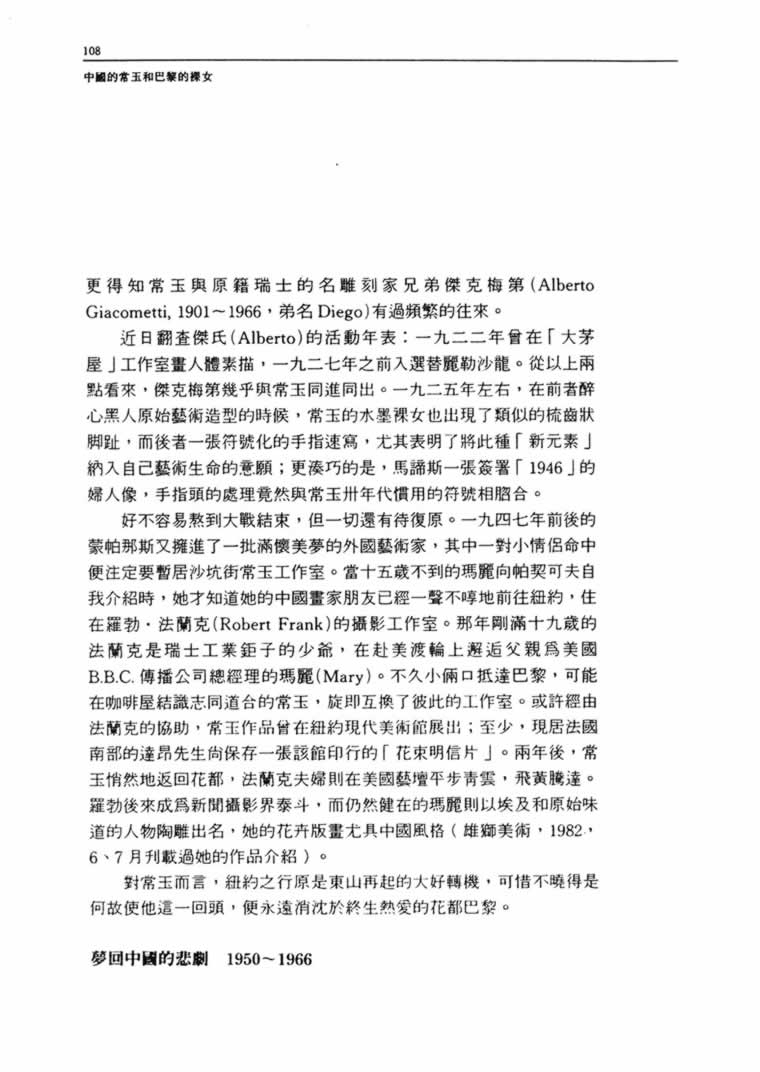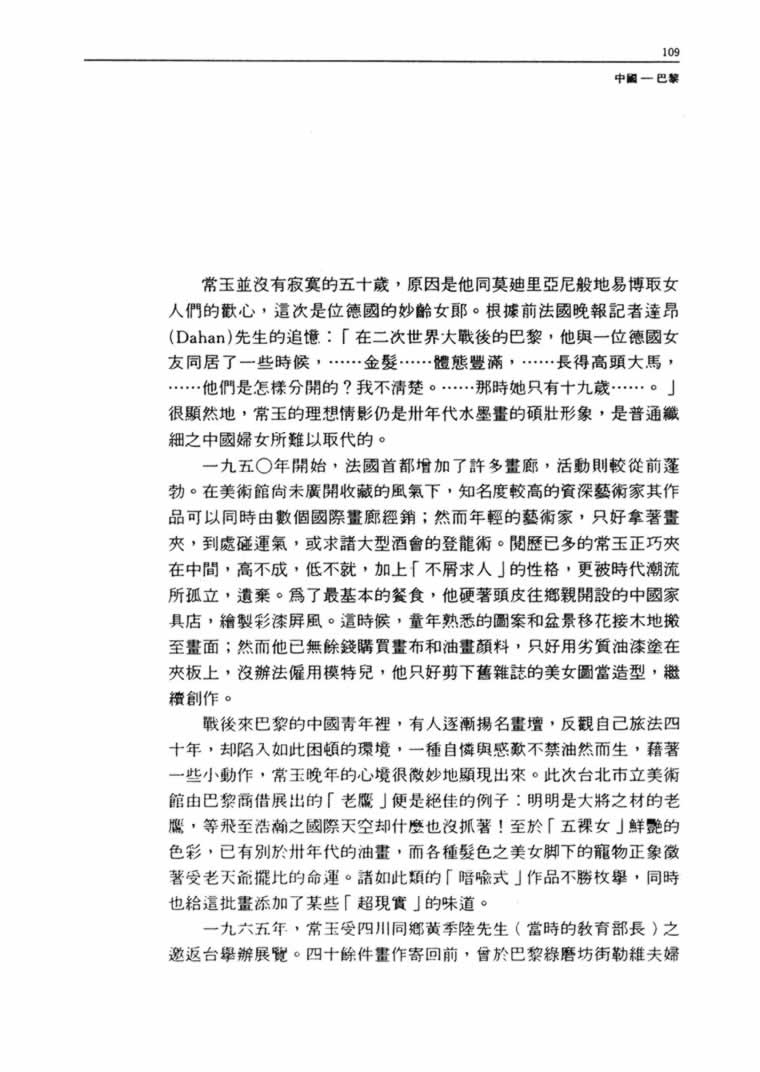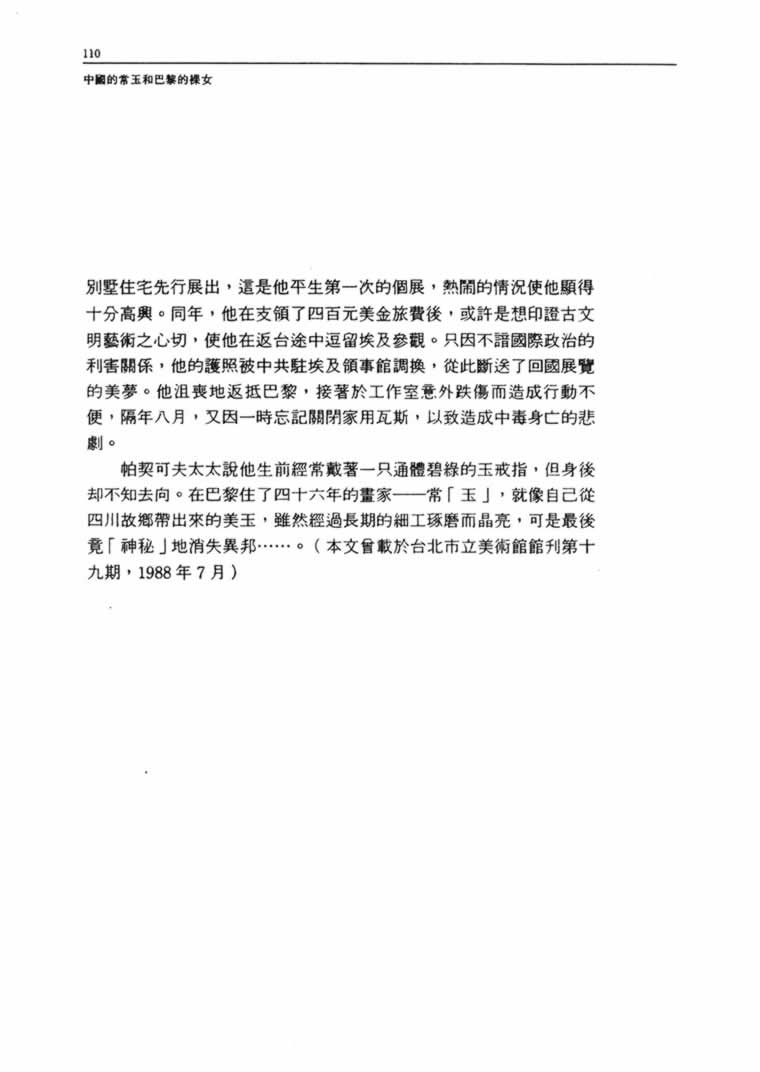早年的藝衛環境1900–1920
因為常玉不喜歡談論自己,加以戰後旅居巴黎的中國藝術家對他的認識都止於皮毛,因此他在法國漫長且富傳奇性的生平更被人渲染得莫測高深。
話說一九八二年,筆者於台北版畫家畫廊展出其作品時,經作家劉咸思女士之介紹,連絡上當年與常玉來往甚密的王季岡先生。七十年前,王先生初見常玉於東京,稍後又結伴赴法國留學。我們彼此雖未謀面,但由加州輾轉而來的三件信函,卻揭開了這位藝術家早年的神秘面紗。「……常玉字幼書,川北順慶人。家有大哥持家,業絲紡,頗豐裕,自嫌讀書少,故力培植弟輩遊學國外,供應費用不缺,使遊學者毋需打工。其在東京九段那張照片,坐者為其二哥常必誠,體稍胖,嗜肉食,善烹調(玉觀摩當有心得),後在滬辦一心牙刷公司,在川採購豬鬃漂白而製,號稱一毛不拔。常玉為畫裝潢圖案。……常玉幼習川宿趙熙字,稱趙字古邃類于右老書法。在東京相遇時,曾示我一日本文藝雜誌,中載有某一橫額書法。人言先書後畫,斯之謂歟。」
從上述粗草的描述,我們得知常玉自幼在四川老家即接受良好的書法陶冶,無怪乎日後字跡能刊載於東京文藝雜誌,而旅居法國時又以水墨勾勒之裸女崛起於巴黎畫壇。暫且不論常玉曾否進入劉海栗創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至少民國十五年左右逐漸傳入上海的西洋油畫一定會引起他的好奇心。特別在東京二哥家作客之際,第一批留歐的日本畫家早已返國廿年,至於到處皆是西洋畫的文部省美術展覽會也有十屆的光景,所以就見識方面來看,常玉比國內的青年藝術家要廣闊得多,而蒙受西潮的衝擊也較深刻。
由東京返回上海短短的期間,常玉不僅準備赴法修習繪畫,還曾替二哥的牙刷公司效勞,從事產品「圖案繪製」的工作,可說是不折不扣學以致用。
巴黎的瘋狂年代 1920–1930
「……民初在東京,川北同鄉都尊常必誠(玉之二哥)如鄉長。其人擅烹調,每邀往大打牙祭,常玉與焉。後同返申江,我北上南開。迨五四輟學,持蔡元培函赴申謁吳稚老,因加入勤工儉學會赴怯,常玉又與焉。此後在法,常常同遊,得觀其作畫。有次告我以劉海栗、王濟遠(上海美專校長、教員)組天馬會自吹自擂,乃與徐悲鴻(公費帶眷留法)、邵洵美(留美習文學,盛宣懷親戚)組天狗會以嘲之……。」
如同王季岡先生信裡娓娓道來的當年往事,常玉是在廿年代初期與勤工儉學會青年同赴法國;然而他抵達巴黎頭幾年的學習和生活細節卻仍舊一片模糊。倘若「蔣碧微回憶錄」所言不假,常玉並未像徐悲鴻般的正式註冊進入國立巴黎美術學校,只是在私設的「人體畫工作室」打打游擊罷了。這與他一向閒散不拘的個性及決心不返列強瓜分下的中國討生活(他曾和王季岡先生談過)有很大的關係。對初抵花都的常玉而言,不免要承擔喜憂參半的複雜感觸:喜的是看到了不再是二手貨的西洋畫真跡;憂的是如何以昔日的基礎在花都加強美的訓練,甚至將它視為自己終生不變的行業!
在常玉尚未摸索出屬於自己創作途徑的當兒,先讓我們概要地瞭解二十年代前半段巴黎本身的文藝環境和活動。
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8)結束不久,恰巧素有「蒙帕那斯王子」之稱的裸女畫家莫迪里亞尼(Modligliani,1884–1920)帶著遺憾病逝慈善醫院。因為飽受戰爭的驚擾,等政治和經濟秩序一恢復,人們乾脆放棄傳統的嚴謹規範和約束,紛紛奉行「即時享樂」之生活哲學,形成了半個世紀後人們所嚮往的「瘋狂年代」( Les Années Folles)。就在一九二五年巴黎時裝界泰斗暨社交名人波勒.普阿黑(Paul Poiret,1879–1944)於艾菲爾鐵塔下的塞納河上,佈置了三艘華麗無比的平底船,入夜後,剛由美國傳來的爵士樂不停地伴奏著,在熱帶奇花和精緻酒食間,穿梭著衣裙短至膝蓋而頭頂小圓帽的國際名媛;至於燈飾和銀質餐具多少都具有德國包浩斯(Bauhaus)設計影響下的幾何造型,也就是當時最時髦的「裝飾藝術」(Les Arts Decoratifs)。是年法國首都所舉辦的「國際裝飾藝術大展」,不僅結合服飾裝潢師和專業藝術家,更進一步地把這種新造型藝術推廣至工商企業。
於相同的巴黎天空下,布賀東(Andre Breton,1896–1966)與好友阿拉貢(Louis Aragon,1897–1987)、蘇波(Philippe Soupault,1897–)業已創辦了鼓吹「超現實主義」的「文學」雜誌(Litterature),而弗洛依德(Freud,1839–1939)和容格(Jung,1875–1961)的心理分析學可說是完備了這羣年輕人的立論。緊接著,畫家馬松(Andre Masson,1896–1987)、達利(Salvador Dail,1904–),以及詩人艾綠亞(Paul Eluard,1895–1952)也加入這個新潮派的文藝團體,而建築師柯布意(Le Corbusier,1887–1965,原名Edouard Jeanneret-Gris)領導的「新精神」(l’Esprit Nouveau)雜誌、足堪代表法蘭西學院的權威性週刊——「文學訊息」(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曾停辦,於1986年底復刊)和「藝術畫冊」(Cahier d’Art),也都相繼問世,使新文藝理論的發表與活動報導達到空前的巔峯。
同是一九二五年,巴黎的藝評家、詩人,以及權威人士,共同選出了當時的「十大藝術家」,排名依序是馬諦斯(Henri Matisse,1869–1954)、麥由(Maillo,1861–1944)、德罕(Andre Derain,1880–1954)、謝公查(Segonzac,1884–1974)、畢卡索(Picasso,1881–1973)、于特里由(Utrillo,1883–1955)、胡奧(Rouault,1871–1958)、波恩納(Bonnard,1867–1947)、布拉克(Braque,1882–1963)、弗拉明克(Vlaminck,1876–1958)。除了畢卡索外,清一色都是土生土長的法國人。其實,寓居於蒙帕那斯附近的巴黎派(l’Ecole de Paris)外籍藝術家不乏才華出眾者,可惜他們獨缺強而有力的畫商及藝評家作後盾,更何況是寄人籬下的異鄉客!這也難怪莫迪(朋友對莫迪里亞尼之暱稱)在喝過酒後,要大聲疾呼:「法國為什麼不能接受義大利藝術?」因此,我們可想像當年巴黎的外國畫家,非但要為「生活」奮鬥,尤須以自己的原籍在法國人面前力爭上游,可說是極其辛苦的。先師李仲生就曾對筆者談過有關藤田嗣治(Foujita,1886–1968)的窘困處境,他說:藤田嗣治曾經窮到把僅餘的幾支油畫筆拿去典賣以糊口…。如今在藝術史上已佔一席之地的夏卡爾(Chagall,1887–1987)、蘇丁(Soutine,1894–1943)、康丁斯基(Kandinsky,1887–1964),及雕刻大師阿其潘可(Archipenko,1866–1944)、查金(Zadkine,1890–1967)等斯拉夫藝術家,廿年代還群聚於「蜂巢大雜院」(La Ruche,是利用博覽會殘存館址改裝的工作室)創作。一到寒冬,大夥兒圍繞爐火前取暖,甚至共用一盞燈泡,可謂十足的波希米亞浪人……。
來巴黎習畫轉眼已五、六載的常玉,住在拉丁區聖米謝大道上小旅館的三樓斗室。據王季岡先生回想他六十餘年前的情形是這樣的:「其人美豐儀,且衣著考究,拉小提琴,打網球,更擅撞球。除此之外,烟酒無緣,不跳舞,也不賭。一生愛好是天然,翩翩佳公子也。外出隨帶白紙簿及鉛筆。坐咖啡館,總愛觀察鄰桌男女,認為有突出形象者,立即素描;亦課外作業自修也。……有時家中匯款未到,無多餘錢,輒啃乾麵包,喝自來水度日。惟一值錢的照像機,時常存入當鋪,或向我告借幾十萬。待家款到,再贖再還。」這部當時富家子才玩得起的照像機,佐證了常玉與徐悲鴻夫婦來往之密切,甚至拍出多幀蔣碧微搔首弄姿的倩影,以及常、蔣兩人打扮時髦的合照。它也意味著巴黎瘋狂年代的放縱自由,不知不覺地感染了某些留學的中國青年。
常玉既然對國立美術學校那種十九世紀式學院派的作風不感興趣,他就只好在「大茅屋工作室」(La Grande Chaumière)與蒙帕那斯的咖啡屋作裸體與肖像素描。那時候,幾乎每天出現在「圓屋頂咖啡屋」(Le Dome)的日本畫家藤田,已逐漸以東方墨線的特點竄紅於畫壇,而「十大藝術家」那趨向單純化的造型和野獸派大膽的用色,不免給常玉留下深刻的印象。莫迪雖含恨離開了蒙帕那斯,但巴黎派裡的裸女畫家卻也相當多,其中較出色的有描繪傷感的波蘭畫家——吉斯令(Kisling,1891–1953)和巴山(Pascin,1885–1930)。巴山原名Pincas,生於保加利亞,父親是西班牙籍猶太人,母親為義大利人。他於一九〇五年初抵巴黎,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遠至北非、古巴、美國等地旅行,一九二二年以美國人身份重返花都,從事水彩素描為主的創作;他偏重於渲染手法的裸女頗得好評,被歸類為抒發個人感性的表現派。這位藝術家放浪形骸的舉止和戲劇性的自殺,為卅餘年後的巴黎投射出另一中國式的倒影——屬於常玉的傳奇性生平。
圓熟期的作品 1930–1940
一九二五年對常玉是相當重要的,因為他已認識自己未來的妻子——哈蒙尼耶小姐(Mlle de la Harmonyère),這可由王季岡先生保存的「凡爾賽宮三人遊」照片得到證實。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常玉為他的法國貴族小姐留下一張喝茶的半身像;紙是隨手在咖啡屋桌上拈來的齒邊餐墊,鉛筆素描的暈染,與藤田、巴山十分類似,只是一雙有神的眸子獨特地反映了四川才子深邃的感情。
或許不願長期罩於他人的畫風之下,常玉改用毛筆與中國水墨作速寫裸女。到底單有東方傳統的書法基礎還是不夠,必須加上藝術家個人對事物特殊的看法和表現,最後一種以俯角具有撼動性的素描遂脫穎而出。雖然廿年代他擁有一部老爺相機,但當時廣角鏡頭尚未出現,他卻能眼測雷同的效果,亦即腳和頭部相較顯得巨大無比而散發著一股強勁的力感。
一張完成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的裸女水彩,只不過草草幾筆墨線與棕、紅彩,都隸屬常玉圓熟期的力和美之結合,自然地洋溢紙上。它已非十九世紀講究比例、線條細膩、看相甜美的寫實閨秀畫;相反地,野獸派和北歐表現主意強調內心感受及直接傳達的特質,早就凝聚在能寫一手好字常玉的筆端。若拿這位帶項鍊的模特兒與名攝影家曼雷(Man Ray,1890–1976)所拍攝之「蒙帕那斯的姬姬」(KiKi de Montparnasse)詳細對照,無論眼神、臉龐和手臂都有驚人的神似。常玉即是活動於蒙帕那斯咖啡屋的畫家,請姬姬當模特兒作畫亦非難事,更何況她的豪爽率直是藝術家間有口皆碑的事實,出身寒微,原名愛麗絲.普罕(Alice Prin,1901–)的姬姬,自大戰末期被一位斯拉夫畫家引進蒙帕那斯以來,因為與藝術家們的充分合作而獲得美譽及愛戴。那個年頭的蒙帕那斯像座小村莊,在那幾家文學咖啡屋裡大夥朝夕相處,有誰不認得誰?莫迪有時剛在義籍廚娘何查莉(Rosalie)的小館晚餐完,突然發現口袋沒錢,抽出畫夾中的素描,一聲道歉,對方也不會嚴拒。廿年代初期,一群巴黎派的畫家就曾在她的牆壁上留下彼此合作的大畫;這些畫作不消幾年光景,都給總明的畫商剝買回去了。於此般「為藝術而藝術」充滿俠氣的純真環境裡,常玉試著尋找自我,結果可以是中國,也可以是巴黎;總之,那該是個沒有國別「真、善、美」的世界。
一九三〇前後數年內,可說是常玉生平最風光得意的時候。最近發現的「徐志摩致劉海粟」信函就如此寫道:「…… 巴黎是有意味,不是?人情的美最令相思無已。常玉家尤其有德有美。……巴黎的風光更有那處可比?我也早晚只想再長翅膀,得往外飛騰。上海生活折死人,怎樣也忍耐不下去!…… 巴黎諸友均候,玉的馬特候候。」此信是一九二九年四月廿五日從上海寄出,劉海栗收到時剛抵達巴黎兩個月。徐志摩所言的「有德有美」,意指甫新婚的常玉夫婦,而浪漫派詩人還念念不忘常玉答應為他畫的馬……。感情上叫徐志摩羨煞的是「神仙美眷」;而在藝術生涯方面,常玉又因巴黎最大收藏家侯謝(Pierre-Henri Roché)的賞識,作品得以和馬諦斯、畢卡索、布拉克等大師之油畫同列一室。此次「中國——巴黎」展中借自巴黎愛德華先生(Dr. Eric Edwards)的「瓶花」及「裸女」,便是輾轉由侯謝舊藏購進的。儘管這兩張空運來台展出的早期油畫,只有白、粉灰等極其簡單的色調,但筆觸卻包含野獸派和表現主義的果敢、直接。大概是以素描為主、油畫輔之之創作風格的關係,一九三二年由格赫(Greud)書店發行,喬瑟(Edouard Joseph)編篡的「1910–1930當代藝術家生平字典」(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es artistes contemporains, 1910–1930)第三冊中「SANYU」一欄的解說是這樣:「常玉,中國畫家,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四日生於四川。以中國水墨所作的速寫和油畫曾參展秋季沙龍及替勒麗沙龍。為法文本「陶潛詩集」製作插圖,該書序文由伯.梵樂希撰寫。」雖然才寥寥幾行,可是在那個種族偏見猶深的年代裡,中國人的名字首次登錄國際性的現代藝術家生平字典中,決非純屬僥倖吧!尤其能與法國大文豪梵樂希(Paul Velery, 1871–1945)相提並論,實在是項殊榮。原來,「陶潛詩集」為旅法學人梁宗岱翻譯,那麼常玉傳世的三張山水版畫插圖,必定是應他的邀請而繪製的。
如果以「終生潦倒」來形容常玉,是不清楚他早年處境的疏忽論斷。從字典、王季岡先生、侯謝夫人的好友,甚至蒙帕那斯碩果僅存的幾位遺老藝術家的口述,筆者費時的層層揭開塵封了六十年的往事。就在昔日光芒重現的同時,巴黎藝擅又被一張廿年代末期的「粉紅色裸女」所震驚;認為它的叫價是三級跳的躍升,連女強人拍賣官的定奪槌也按捺不住……。畫中酷似姊妹花的一雙裸女,有著畢卡索巨人派階段的誇張,但卻被輕柔的粉色調、漆黑背景及中國圖案的鏤花白紗所沖淡。新主人是花都的年輕貴婦,縱使筆者尚未能撥空造訪,相信她必能用一種東方寧靜祥和的語言和它對談,就像六十二年前哈蒙尼耶男爵的女兒跟她的中國情郎一般……。
二次大戰前後的轉機 1940–1950
徐悲鴻、潘玉良、龐薰琹和劉海栗一個接一個返回中國本土,不是繼續畫畫,就是從事藝術教育工作。居留巴黎最久的常玉於中國朋友走光後,連結褵才幾年的法籍妻子也離他而去。機會性地賣畫和家中的匯款尚足讓他走動在蒙帕那斯各咖啡屋間;畢竟,習慣了巴黎的自由浪漫,國內保守的社會風氣絕對喚不回這位漂泊異鄉的遊子。可能為龐薰琹所邀,一九三二年加入野獸派與新古典風格的「決瀾社」,而郵寄作品參展算是常玉和國內唯一的連繫。八四年返台時,我嘗以此就教過李仲生老師,他說:「常玉與龐薰琹的交情尚好,凡事他比較清楚……。」
一九四〇年左右,常玉因兄長故去,不得已回四川老家。那是廿年來第一次,也是生平最後一次返鄉。帶著分家豐盛的財產重返法國,不擅理財公子哥兒脾氣的他,又在短時間內落得兩袖清風。卅年代初期由蜜斯坦也(Mistinguett)唱紅的「跟我訴說著愛」,以及那首廣受歡迎由美國黑人女歌手貝克(Josephine Baker)用甜而不純正的法語唱出的「粉紅色人生」,早就在德軍坦克進駐巴黎的隆隆聲中淹沒了。猶太畫商往英、美等國竄逃,名畫家畢卡索也帶著家人至西海岸避難。那時常玉已搬進離蒙帕那斯不遠的沙坑街藝術家工作室,與一位俄裔女雕刻家帕契可夫太太毗鄰而居。據她說:「常玉曾嘗試雕刻和陶藝,於物質環境艱難的戰時,幸賴自己製作的陶器託售維生……。」四年前,有緣結識常玉五十年代的密友——勒維夫婦(Lévy),才得以在他們家中看到常玉的動物陶雕。俄裔猶太籍的勒維夫人經營絲綢生意,早年活動於超現實藝術家的圈子;由她的口中更得知常玉與原籍瑞士的名雕刻家兄弟傑克梅第(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弟名Diego)有過頻繁的往來。
近日翻查傑氏(Alberto)的活動年表:一九二二年曾在「大茅屋」工作室畫人體素描,一九二七年之前入選替麗勒沙龍。從以上兩點看來,傑克梅第幾乎與常玉同進同出。一九二五年左右,在前者醉心黑人原始藝術造型的時候,常玉的水墨裸女也出現了類似的梳齒狀腳趾,而後者一張符號化的手指速寫,尤其表明了將此種「新元素」納入自己藝術生命的意願;更湊巧的是,馬諦斯一張簽署「1946」的婦人像,手指頭的處理竟然與常玉卅年代慣用的符號相吻合。
好不容易熬到大戰結束,但一切還有待復原。一九四七年前後的蒙帕那斯又擁進了一批滿懷美夢的外國藝術家,其中一對小情侶命中便注定要暫居沙坑街常玉工作室。當十五歲不到的瑪麗向帕契可夫自我介紹時,她才知道她的中國畫家朋友已經一聲不哼地前往紐約,住在羅勃.法蘭克(Robert Frank)的攝影工作室。那年剛滿十九歲的法蘭克是瑞士工業鉅子的少爺,在赴美渡輪上邂逅父親為美國B.B.C.傳播公司總經理的瑪麗(Mary)不久小倆口抵達巴黎,可能在咖啡屋結識志同道合的常玉,旋即互換了彼此的工作室。或許經由法蘭克的協助,常玉作品曾在紐約現代美術館展出;至少,現居法國南部的達昂先生尚保存一張該館印行的「花束明信片」。兩年後,常玉悄然地返回花都,法蘭克夫婦則在美國藝壇平步青雲,飛黃騰達。羅勃後來成為新聞攝影界泰斗,而仍然健在的瑪麗則以埃及和原始味道的人物陶雕出名,她的花卉版畫尤具中國風格(雄獅美術,1982,6、7月刊載過她的作品介紹)。
對常玉而言,紐約之行原是東山再起的大好轉機,可惜不曉得是何故使他這一回頭,便永遠消沈於終生熱愛的花都巴黎。
夢回中國的悲劇1950–1966
常玉並沒有寂寞的五十歲,原因是他同莫迪里亞尼般地易博取女人們的歡心,這次是位德國的妙齡女郎。根據前法國晚報記者達昂(Dahan)先生的追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他與一位德國女友同居了一些時候,……金髮……體態豐滿,……長得高頭大馬,……他們是怎樣分開的?我不清楚。……那時她只有十九歲……。」很顯然地,常玉的理想倩影仍是卅年代水墨畫的碩壯形象,是普通纖細之中國婦女所難以取代的。
一九五〇年開始,法國首都增加了許多畫廊,活動則較從前蓬勃。在美術館尚未廣開收藏的風氣下,知名度較高的資深藝術家其作品可以同時由數個國際畫廊經銷;然而年輕的藝術家,只好拿著畫夾,到處碰運氣,或求諸大型酒會的登龍術。閱歷已多的常玉正巧夾在中間,高不成,低不就,加上「不屑求人」的性格,更被時代潮流所孤立,遺棄。為了最基本的餐食,他硬著頭皮往鄉親開設的中國家具店,繪製彩漆屏風。這時候,童年熟悉的圖案和盆景移花接木地搬至畫面;然而他已無餘錢購買畫布和油畫顏料,只好用劣質油漆塗在夾板上,沒辦法僱用模特兒,他只好剪下舊雜誌的美女圖當造型,繼續創作。
戰後來巴黎的中國青年裡,有人逐漸揚名畫壇,反觀自己旅法四十年,卻陷入如此困頓的環境,一種自憐與感歎不禁油然而生,藉著一些小動作,常玉晚年的心境很微妙地顯現出來。此次台北市立美術館由巴黎商借展出的「老鷹」便是絕佳的例子:明明是大將之材的老鷹,等飛至浩瀚之國際天空卻什麼也沒抓著!至於「五裸女」鮮豔的色彩,已有別於卅年代的油畫,而各種髮色之美女腳下的寵物正象徵著受老天爺擺比的命運。諸如此類的「暗喻式」作品不勝枚舉,同時也給這批畫添加了某些「超現實」的味道。
一九六五年,常玉受四川同鄉黃季陸先生(當時的教育部長)之邀返台舉辦展覽。四十餘件畫作寄回前,曾於巴黎綠磨坊街勒維夫婦別墅住宅先行展出,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的個展,熱鬧的情況使他顯得十分高興。同年,他在支領了四百元美金旅費後,或許是想印證古文明藝術之心切,使他在返台途中逗留埃及參觀。只因不諳國際政治的利害關係,他的護照被中共駐埃及領事館調換,從此斷送了回國展覽的美夢。他沮喪地返抵巴黎,接著於工作室急外跌傷而造成行動不便,隔年八月,又因一時忘記關閉家用瓦斯,以致造成中毒身亡的悲劇。
帕契可夫太太說他生前經常戴著一只通體碧綠的玉戒指,但身後卻不知去向。在巴黎住了四十六年的畫家——常「玉」,就像自己從四川故鄉帶出來的美玉,雖然經過長期的細工琢磨而晶亮,可是最後竟「神秘」地消失異邦……(本文曾載於台北市立美術館館刊第十九期,198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