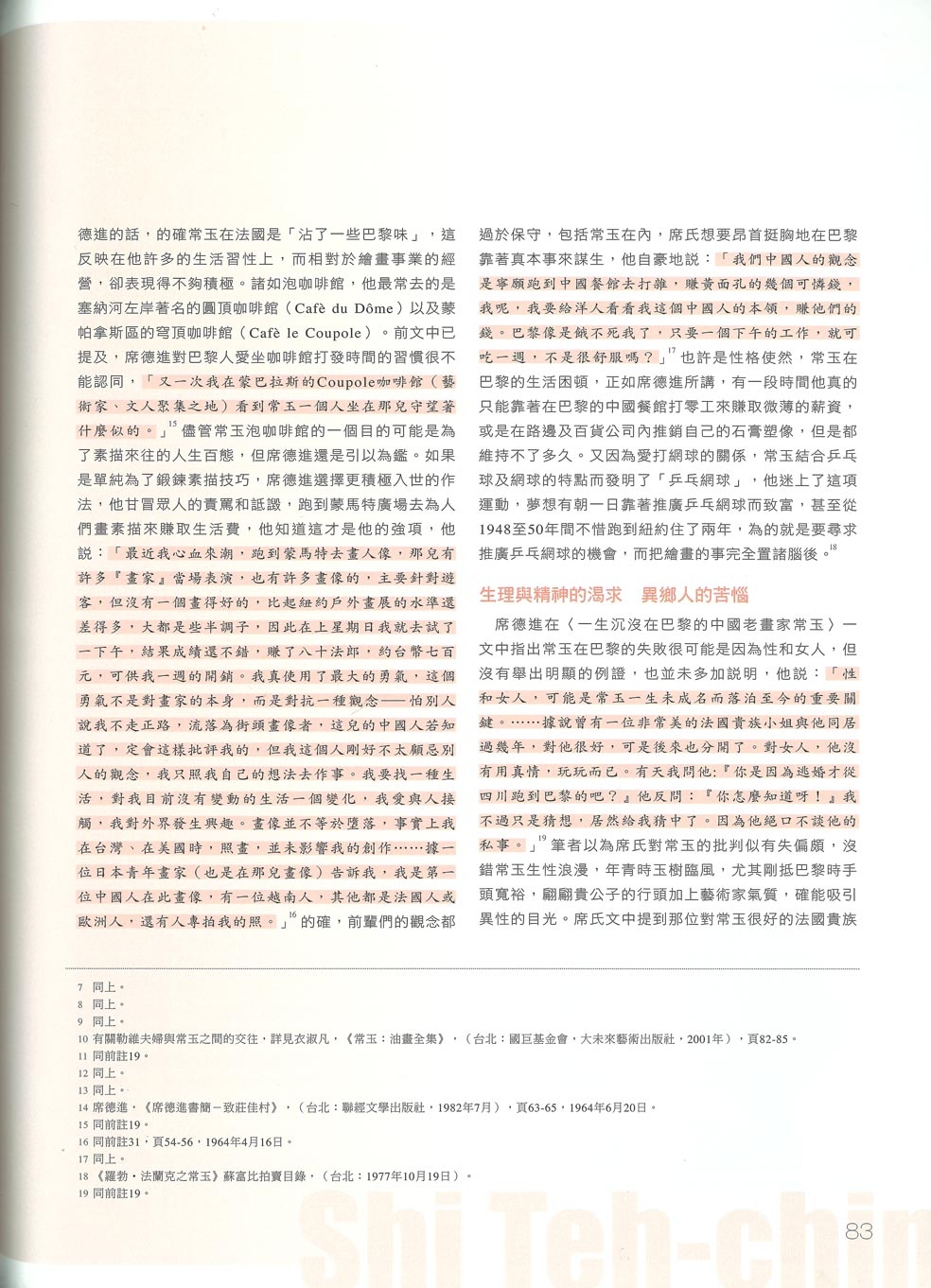班雅明曾說,因為波特萊爾,巴黎首度成為一首抒情詩的主題。為了這首夢想之詩,如同畢卡索、馬諦斯、海明威、費茲傑羅、布紐爾等遍及繪畫、文學、電影等領域的傳奇人物,常玉、席德進,亦先後投入這場流動的饗宴。他們也和海明威一樣在河左岸的圓頂咖啡館廝混,那裡聚集了一眾遊手好閒的人們,他們扯淡、哈錢、忍飢、啃書、泡咖啡館,他們揣著夢想而百無聊賴。席德進曾說:「巴黎是最令人迷醉的城市,一個藝術家到了她的懷裡,隨你如何來塑造自己,都可以。」他和常玉都曾緊緊摟著這個大城小夢,儘管夢醒魂斷,但短暫相遇擦身而過的兩人,最終留下了那一去不復返的美好年代,一段很窮卻滿溢夢想的日子。
造化弄人,是甚麼樣的機緣,甚麼樣的時空背景底下,讓1901年出生的旅法畫家常玉跟1923年出生的旅台畫家席德進得以有所交會?常玉比席德進年長超過二十歲,除了兩人皆熱愛藝術,又都出生並成長於中國四川以外,兩位畫家的學經歷、成就以及作品風格等是否還有其它的異同點,值得我們多作深究的呢?
1901年,常玉出生於四川省南充市,自幼即對藝術展現濃厚興趣,曾先後跟隨父親常書舫習畫以及四川名儒趙熙(1877-1938)習書法,打下良好的書畫根基。1921年留學巴黎,除於1926年到27年間曾短暫回國,此後便一直待在異鄉闖蕩,終生未再踏足故土。他待在巴黎四十多年,發展並不順遂,1966年因瓦斯中毒客死異鄉,身後蕭條,直至過世近三十年後畫名才被重新提起,畫價也在市場上節節攀升,沈睡了這麼多年,終於揚眉吐氣為世人所重視,並還給他應得的榮耀。
巴黎 夢想之地
常玉比席德進年長二十多歲,兩人卻先後來到巴黎,常玉是屬於第一批從中國大陸赴法修習藝術的先鋒,他抵達巴黎的時候,正藉西方美術史上所謂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那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比起歐洲那些飽受戰火摧殘的國家來說,巴黎算是相對穩定及開放的,因此吸引了一批不同國籍的藝術家們紛紛來此落脚,他們群聚於蒙帕拿斯(Monparnasse)及蒙馬特山(Monmartre)一帶,儘管平均的生活條件比較差,但多半流露出對藝術的熱愛,在創作上各自表現出本身的民族特色,並不隨波逐流。這些藝術家的創作題材廣泛,從巴黎街景到近郊森林,從裸女到農夫,從生活小景到夢幻般的場景等等……代表人物包括莫迪里亞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 Lautrac,1864-1901)、蘇汀(Chaïm Soutine,1894-1943)、尤特里羅(Maurice Utrillo,1883-1955)、夏卡爾(Marc Chagall,1887-1985)、奇斯林(Moïse Kisling,1891-1953)等,這些來自不同國度的藝術家們不管是受立體派、後期印象派、野獸派等的影響,都在作品中摻入了對自身國家的信仰及鄉愁,再以豐富的色彩及情感訴諸畫面,畫風不容易歸類,因此被統稱為「巴黎畫派」,盛行的時間涵蓋了二十世紀初到1930年代之間。台灣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李明明教授對「巴黎畫派」的誕生有過精癖的見解:「巴黎畫派」(Ecole de Paris)一詞大約出現在20年代初,指由世界各地因為嚮往現代藝術,不約而同來到巴黎,主要活動於蒙帕那斯一帶的畫家,……事實上,巴黎畫派不僅指畫家、雕刻家,還有不少文學家如海明威、史坦貝克,以及音樂家、劇作家,他們都加入了當時不休不眠的藝術家聚會。因此「巴黎畫派」一詞並不是由藝術風格(如印象派)而產生的名稱,它涵蓋了一特定時空範圍內的藝術活動現象;更精確地說,它指稱兩次歐戰間,以巴黎蒙馬特和蒙帕那斯地區為活動場域的藝術家群,其共同點在一種波西米亞流浪詩人的氣質以及藝術家敏銳而又脆弱的感性訴求。(註1)
常玉出生的年代剛好碰上中國受到西方文明的入侵,學術界普遍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家鼓勵年青人出洋留學,並提供經費的支援,期望他們回國後能從多方面改革傳統,而對於想進修藝術的人來說,巴黎這個當年的藝術之都固然是首選無疑。常玉欣逢其盛,亦躋身西方取經的第一代華人藝術家之流。常玉出生於四川富商之家,少年時代曾隨二哥常必誠(1883-1943)留學東洋,回國後受蔡元培(1867-1940)勤工儉學運動的鼓吹,於1921年由經營繅絲廠的長兄常俊民(1864-1931)出資赴巴黎習藝術。迥異於同期以公費赴歐學畫的一批藝術家如徐悲鴻(1895-1953)、林風眠(1900-1991)及龐薰琹(1906-1985)等人,他們大多抱持著報效祖國的心,在學成後回國從事美術教育的改革,常玉因為成長背景的關係,壓根子沒有這種偉大的抱負和使命感。他初抵巴黎時生活不虞匱乏,選擇前往不屬於學院派的大茅屋學院習畫,不受拘束地體驗西方的素描技巧,過著如貴公子般的生活,閒時愛往郊外踏青、拉小提琴、打網球、交女朋友或是安逸地待在咖啡館內素描眾生。生性浪漫不羈的他在花都如魚得水,迅速地以非學院派之姿在畫壇闖出了一點知名度,並受到著名藝術收藏家兼經紀人亨利.皮爾.侯謝(Henri-Pierre Rochè,1879-1959)的賞識,一度有望成為畫壇的明日之星。他畫動物、裸女及瓶花等,作品隱含中國毛筆的功力及東方書法線性的柔美,大有機會晉身為「巴黎畫派」的東方代表人物,可惜因為性格的問題,最終事與願違,結果畫商所捧紅的是同樣來自東方的日裔畫家藤田翤治!
落難才子與巴黎過客
藤田嗣治(Léonard Fujita,1886-1968)比常玉年長一些,早於1913年便已來到巴黎,與「巴黎畫派」的畫家如畢卡索、馬諦斯及莫迪里亞尼等皆熟稔。1921年憑藉三幅參展巴黎沙龍的畫作而聲名鵲起。常玉的畫作明顯受到藤田的影響,無論在題材與技巧上,都有著頗多藤田早期的影子,不過相互影響向來是「巴黎畫派」藝術家之間的一項特色。藤田在巴黎的社交圈很活躍,作品又極富東方人敏感含蓄的特質,因此順理成章取代了常玉,儼然成為巴黎畫派的東方代表。我們現在回頭看,藤田與常玉在巴黎時的活動範圍都集中在蒙帕拿斯一帶,二人皆不約而同把1930年代西歐現代藝術的特質納入自己的作品中,畫面兼具東方繪畫的精煉細膩與西方現代繪畫的感性訴求,兩者無疑都應該被歸納為「巴黎畫派」藝術家,不過筆者認為若就國際知名度來說,常玉還是遠遠落後於藤田的。常玉自小衣食無缺,沒有金錢管理的概念,加上天性浪漫,花錢如流水,加上1929年家中遭逢變故,先是家族經營的絲廠業務衰退,接著1931年長兄身故,來自家鄉的經濟支援完全斷絕,他在巴黎的生活頓入困境,變得無所適從,只能憑藉好友的接濟,由於不擅與畫商溝通合作,更平白錯失了成名的契機,只好獨自在巴黎奮鬥了四十多年,最終默默無聞,客死異鄉。又因走得突然,身邊無親無故,被草草埋葬在巴黎近郊的荒塚,身後二十多年無人聞問,直至1980代末才又為世人提起,並對他在畫壇的成就給予重新定位。
事實上常玉這名字很早就印入了席德進的腦海中,在他1971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一生沉沒在巴黎的中國老畫家常玉〉中,清楚的交待了與常玉在巴黎交往的過程:「說來真是奇妙,早在三十年前(1941),我就在龐薰琹老師家裏看到常玉的畫,聽到他的名字。那時我才剛進成都省立藝專開始學畫。在華西壩龐老師的家裡看畫,老師指著牆上一幅單線條的毛筆速寫說:『這位是你們四川老鄉,他的畫非常出色。』速寫一個裸女坐著抽煙的姿態,有點馬諦斯的畫風,卻帶中國畫的意味。」(註2)龐薰琹是席德進在四川省立技藝專科學校時的美術老師,與常玉一樣曾在巴黎大茅屋學院習素描,與常玉素有往來,龐氏早期的畫作甚至帶有常玉的影子,席氏在老師的家裏看到常玉的畫作是順理成章的。龐薰琹曾經講過常玉對正統學院式訓練向來不屑一顧,他傾向於自由而無規範的表現形式。(註3)沒想到事隔二十多年之後在巴黎得以與常玉會面:「……1963年我到了巴黎,在一個中國留法學人的畫展集會裏,才碰見常玉。」(註4)那時候的常玉已經六十多歲,席氏對他的第一印象是:「個子不高,平頭,帶一付老光眼鏡,略粗寬的身材,藏在大衣裏,顯得十分潦倒。」(註5)也許是一種出於對同鄉的關切以及對一位前輩畫家的惺惺相惜,席氏對常玉在巴黎的生活及經歷產生了莫大的好奇,他當下就決定要把常玉的故事寫出來,作為後人的一個警愓。「由於前後的種種因素,常玉這個人就對我發生了神袐而奇妙的吸引力,使我想去探討他在巴黎籍籍無名而活著,畫著的原因。他不是沒有天才,反之,他天賦頗高,說他不努力吧?他的畫可比許多人都強。然而他畢竟在這藝術之都沉沒了!每天靠三個法郎(約合24元台幣)過活下去。我當時想:『我要把常玉的故事寫一部書——一個被埋沒的天才畫家,一個失敗者的傳記。人們多半歌頌成功者的傳記,為甚麼不寫一個失敗者的一生呢?也許由於他的失敗,才更能給予後人以警惕哩。』」(註6)就這樣鋪展出兩人的交往。
席德進到處向巴黎的朋友打聽有關常玉的種種,但大家知道的好像都相當有限,於是他登門拜訪了常玉位於沙坑街28號的工作室,他回憶道:「一天我到他畫室去拜訪他,他住在巴黎的十四區,這間畫室對一個無名而潦倒的老畫家來說,是太好了。第一不爬樓梯,第二非常寬敞而明亮,有高大的玻璃窗,一個閣樓上是他的臥室,一個小廚房擺滿了他親自作的四川味調味品。畫室靠窗和牆上都是他的畫,桌上的東西十分雜亂,恐怕三十年來就是如此。地上散些油漆罐子。他總是在房中轉來轉去找東西,我看他記憶力是很差了。口裏一直咕嚕著。」(註7)席德進回想當他剛認識常玉時,對方的話還不太多,態度帶點保留,:「我以對待一位長輩親人般的心情和他攀談,他起初並不十分信任一個像我這樣陌生而比他晚來巴黎的中國人。常常是我問得多,他答的少,支吾幾句罷了。人卻不壞,我了解這是畫家的怪癖。」(註8)不過也許是同鄉人異地相逢分外親切,那天的造訪打破了彼此間的隔閡,常玉最後不但搬出很多畫作給席德進欣賞,更大方地留他下來用餐,甚至親自下廚,以拿手的家鄉菜餚款待客人,:「那天中飯留我下來吃他親手做的菜,他一手道地的四川菜,巴黎的中國人沒有不知曉的。一盤炒腰花,一大碗牛肚和豬脚燉的濃湯、泡菜、乾烤的糖酥餅,實在好吃。飯後他取出他年青時一張照片,真可說是一位風度翩翩的美男子。如今的他髮已斑白,聽覺也不行了。帶點老態,脾氣古怪,口裏咒駡著。」(註9)
短暫的拜會結束,1965年12月17日席德進受邀出席了常玉在艾田及娜塔沙.勒維夫婦(Natacha & Etienne Lèvy)家所舉辦的一次個展,其中包括勒維夫婦的眾多好友,而中國籍畫家出席的並不多,只有潘玉良(1895-1977)、趙無極及朱德群等人,只是大家都沒想到這次展覽竟成了常玉生平最後的一次個展。(註10)席氏回憶當晚的狀況:「……1965年的12月,他的猶太朋友,一對青年夫婦幫助他,在他們家裡為他舉行了他(可能是一生中的首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個展。畫掛滿了客廳和走廊……展出的作品中,有幾幅人體,僅以粗黑單純的線構成的油畫,奇特而表現著性感。帶點普普畫的意味。他也畫了荷花、菊花、山茶花,作了幾件馬的雕塑,塗以彩色。並展出一個屏風,他特別拉我到屏風的背面,指點給我看他用小楷書寫滿了的金瓶梅中的詞句,以及男女之間媾和的私情。」(註11)四個月之後,當席德進決定離開巴黎回台灣,沒想到與他算不上深交的常玉居然大老遠的跑到機場來為他送行,對於常玉的熱情體貼,儘管可能只是出於對晚輩同鄉的一份情誼,席德進還是銘記在心:「我最後一次跟常玉見面,是在1966年3月底一個傍晚,我起程回國,正要離開巴黎飛往羅馬。他到巴黎的航空終站Invalides來為我送行。他精神很好,以外國人的眼光看他,也不過五十多歳的人吧,但你若想打聽他的年紀,或問他在巴黎三四十年來是怎麼過活的?他就顧左右而言他了。當晚我把一件厚實毛外衫送給他,誰知就此與他永訣。」(註12)是的,他萬萬料想不到與常玉的交往就此劃下句點,等他回到台灣數個月以後的8月12日,常玉便因瓦斯中毒在自家的畫室內與世長辭,享年66歲,結束了在異鄉悲苦奮鬥的一生。
對一個同樣來自中國而在巴黎打拼尋求成名機會的藝術家而言,透過與常玉的接觸,席德進從這位前輩畫家身上看到的是一個失敗者的經驗,因此想把對方的故事寫下來,作為對後來者的警惕,只是他也許沒想到這當中被影響最直接也最深刻的,恐怕還是他自己。席德進頗欣賞常玉畫作的樸實無華,他說:「……但是他的畫卻是那麼樸實,像一個四川鄉下人染了一點巴黎味,誠懇而沒有矯飾。」(註13)他覺得常玉不是沒有成名的條件,只是礙於客觀環境及自身性格,終究使他抑鬱不得志。在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他這麼分析:「在此想要成名,必須終生住下來,必須你的作品與眾不同,有新的創意,必須長久的磨鍊,最後還要看機運好不好,遇到有人提拔才行。我們東方人,在此想被人重視,非得有過人之表現,好到眾人承認才能出頭,因為我們是外國人。法國他們是捧自己的畫家,到了外國,我們才覺得國家的背景與力量,對個人的成功,有絕對重要的因素。美國人捧自己的畫家,英國政府也一樣為他們的畫家宣傳,而我們卻只有孤軍作戰。西方人看我們東方人總不夠了解而存有偏見。東方畫家在此成名的只有二人,戰前的藤田嗣治(日本人),戰後的趙無極(日本有位抽象畫家Sugai在此地也很有名,紅過一時,但目前已聽不到他的大名了。)趙無極的成功,第一是他真有本領,來的時候恰是戰後抽象畫興起之際,第二是他遇到了幾位大批評家及法國文化部的官員而捧他出名的,還有他的錢,這些因素,是缺一不可。」(註14)常玉是終生住在巴黎沒有錯,畫作亦頗具個人特色,也不是沒有成名的機會,但他始終無法在異鄉突圍,這大概只能歸咎於性格上的盲點吧。首先因為出身富裕,缺乏金錢概念,年青時的貴公子習染,讓他平白錯失了與畫商合作的契機。借用席德進的話,的確常玉在法國是「沾了一些巴黎味」,這反映在他許多的生活習性上,而相對於繪畫事業的經營,卻表現得不夠積極。諸如泡咖啡館,他最常去的是塞納河左岸著名的圓頂咖啡館Cafè du Dôme以及蒙帕拿斯區的穹頂咖啡館(Cafè le Coupole—)。前文中已提及,席德進對巴黎人愛坐咖啡館打發時間的習慣很不能認同,「又一次我在蒙巴拉斯的Coupole咖啡館(藝術家、文人聚集之地)看到常玉一個人坐在那兒守望著甚麼似的。」(註15)儘管常玉泡咖啡館的一個目的可能是為了素描來往的人生百態,但席德進還是引以為鑑。如果是單純為了鍛鍊素描技巧,席德進選擇更積極入世的作法,他甘冒眾人的責駡和詆譭,跑到蒙馬特廣場去為人們畫素描像來賺取生活費,他知道這才是他的強項,他說:「最近我心血來潮,跑到蒙馬特去畫人像,那兒有許多『畫家』當場表演,也有許多畫像的,主要針對遊客,但沒有一個畫得好的,比起紐約戶外畫展的水準還差得多,大都是些半調子,因此在上星期日我就去試了一下午,結果成績還不錯,賺了八十法郎,約台幣七百元,可供我一週的開銷。我真使用了最大的勇氣,這個勇氣不是對畫家的本身,而是對抗一種觀念─怕別人說我不走正路,流落為街頭畫像者,這兒的中國人若知道了,定會這樣批評我的,但我這個人剛好不太顧忌別人的觀念,我只照我自己的想法去作事。我要找一種生活,對我目前沒有變動的生活一個變化,我愛與人接觸,我對外界發生興趣。畫像並不等於墮落,事實上我在台灣、在美國時,照畫,並未影響我的創作……據一位日本青年畫家(也是在那兒畫像)告訴我,我是第一位中國人在此畫像,有一位越南人,其他都是法國人或歐洲人,還有人專拍我的照。」(註16)的確,前輩們的觀念都過於保守,包括常玉在內,席氏想要昂首挺胸地在巴黎靠著真本事來謀生,他自豪地說:「我們中國人的觀念是寧願跑到中國餐館去打雜,賺黃面孔的幾個可憐錢,躱起來,我呢,我要給洋人看看我這個中國人的本領,賺他們的錢。巴黎像是餓不死我了,只要一個下午的工作,就可吃一週,不是很舒服嗎?」(註17)也許是性格使然,常玉在巴黎的生活困頓,正如席德進所講,有一段時間他真的只能靠著在巴黎的中國餐館打零工來賺取微薄的薪資,或是在路邊及百貨公司內推銷自己的石膏塑像,但是都維持不了多久。又因為愛打網球的關係,常玉結合乒乓球及網球的特點而發明了「乒乓網球」,他迷上了這項運動,夢想有朝一日靠著推廣乒乓網球而致富,甚至從1948至1950年間不惜跑到紐約住了兩年,為的就是要尋求推廣乒乓網球的機會,而把繪畫的事完全置諸腦後。(註18)
生理與精神的渴求 異鄉人的苦惱
席德進在〈一生沉沒在巴黎的中國老畫家常玉〉一文中指出常玉在巴黎的失敗很可能是因為性和女人,但沒有舉出明顯的例證,也並未多加說明,他說:「性和女人,可能是常玉一生未成名而落泊至今的重要關鍵。……據說曾有一位非常美的法國貴族小姐與他同居過幾年,對他很好,可是後來也分開了。對女人,他沒有用真情,玩玩而已。有天我問他:『你是因為逃婚才從四川跑到巴黎的吧?』他反問:『你怎麼知道呀?!』我不過只是猜想,居然給我猜中了。因為他絕口不談他的私事。」(註19)筆者以為席氏對常玉的批判似有失偏頗,沒錯常玉生性浪漫,年青時候玉樹臨風,尤其剛抵巴黎時手頭寬裕,翩翩貴公子的行頭加上藝術家的氣質,確能吸引異性的目光。席氏文中提到那位對常玉很好的法國貴族小姐,事實上正是常玉的太太瑪素.夏綠蒂.哈祖尼耶(Marcelle Charlotte Guyot de la Hardrouyẻre,1904-),當年年青貎美的瑪素就是在大茅屋工作室上素描課時認識常玉,她傾慕於對方獨特而有力的素描才華,兩人迅即熱戀並同居,1928年步入禮堂,婚後他們有過一段極甜蜜恩愛的時光,可惜後來瑪素因懷疑常玉對他不忠而堅持與他離婚,這段短暫的婚姻只維持了三年,此後常玉終生未再踏入婚姻。
常玉愛女人,尤其是金髮、身材高壯的外國美女,他對異性的敏銳觀察力及審美標準反映在他大量的裸女素描中。可能是年青時的氣燄,加上婚姻失敗,妻子求去,很自然被人(尤其是巴黎的華人圈)渲染成花花公子之流,但從婚姻這事情上看他卻不失為一個專一的人,至少比起西方的畢卡索及東方的張大千(1899-1983),常玉並沒有三妻四妾,他的浪漫不覊其實還不至於墜落,他對性的索求充其量只為了排解在異鄉的寂寞而已。套用席德進的話:「你想戀愛,而又苦無對象,這是很苦惱的,我有時也是,幾乎每天都需要戀愛,這是人生理與精神的渴求,應該使它得到滿足。在你的環境裡,也許太狹窄,不容易找到,在這兒(按:指巴黎),一般人對性的生活,就比較能隨心滿足,你總可找到你所需要的。」(註20)反觀席德進自己的同性情慾,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見得太認真,在寫予友人的信中,就曾多次透露在巴黎的一些性愛體驗:「有晚,我遇見一位法國軍人,二十歲,很美,到我這兒,我為他畫了一張像,他是里昂人,我們玩到午夜,他才回營。當然,以後也不會再見到他了,外國人不像中國人,可以保持往來,這種偶然相遇的朋友,只有一次!」(註21)又說:「在巴黎男人與男人一起的事是極平常的,紐約、倫敦也一樣,尤其是藝術家們。我最近遇到一位很美的人,『玩』了一次,大都是玩了一次,就不再相逢了,假如你要追求性的滿足,巴黎是最好的地方……」 (註22)不管是異性戀的常玉,或是同性戀的席德進,二者在感情上皆無法獲得持久穏定的伴侶,對於兩位同樣是身處異鄉又生性浪漫的藝術家來說,這種速食的愛情,大抵是很難避免的吧!由於常玉對私生活始終保持十分低調,我們實在不宜輕易下定論說性與女人是足以構成他在巴黎沉淪的一個主因,但毋庸置疑的是,如同大部份巴黎畫派的藝術家一般,性好比潤滑劑,能激發創作動能,確保他有源源不絕的靈感,並因而讓他留下了很多不朽的裸女畫作。
席德進覺得常玉的潦倒還得歸咎於其低調又含蓄的性格:「他認為畫不成熟,就不該拿出去展覽。他不喜歡張揚,可能就因為這樣太含蓄了,才把自己禁錮著,慢慢地失去了衝勁,默默無聞迄今。(註23)相對的,席德進則勇於表現自我,他曾經講過:「假如你有真本領,最好讓識貨的人知道,你就不會被埋沒。」(註24)也許就是這種積極不服輸的個性,讓他體會到想在巴黎成功,就不能像常玉這樣漫不經心,相反的,他非常主動,在1965年1月初寫給友人的信中,他信心滿滿地說道:「在這兒有些學畫的人,根本不敢把畫拿給畫廊看,而我,則勇氣百倍。有次夏陽比我先找到了畫廊,我就被他激起了,非找到畫廊來看我的畫不可,他近來三個月忙於修房子,未動筆,而我在這三個月中,畫大有進展,畫廊也找到了三、四處願意來我畫室看畫了,我現在追到他前面。─這兒畫廊選一個畫家,先得帶畫去給看兩次,然後喜歡了,才決定到畫室看,最後才給你開畫展,畫展若人家批評好,賣得出去,畫廊才會與你訂合同。我現在加緊往上爬,在台灣我已爬到了最高峰,但在巴黎,我才開始。」(註25)然而沒想到,就在他如願在巴黎舉行了個展之後,他卻又慢慢萌生了不如歸去的念頭,並且在一年後付諸行動,毅然決然地告別巴黎,對之前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好像又一點都不覺惋惜。他說:「我知道多少在台灣的朋友,在羨慕我有今天,但我到了今天愈來愈迷惑與矛盾,不知如何是好,我常常想回台灣,但又不知到底該如何來決定我的一生。我離開自己的國土,像無法在別處生根(藝術上的),我需要自己的土地來滋養我。也許我是有堅強的信心與勇氣的,但隨年齡的增長,我的心在變質。我失去了信心,我已堅強地支持了這麼多年,現在像面臨崩潰了(精神上的),我像失去了目標,手足無措似的,也許這是我一時的迷失,這就是我目前的精神狀態。」(註26)
他深切體會到要在巴黎成名必須要趁年青,那兒的機會是屬於年輕人的,常玉就因為年青的時候沒能好好把握成名的契機,結果機會稍緃即逝:「在巴黎要想打個出路最少需要五年的時間,我因為年齡的關係,有許多青年畫家們的大畫展都無法參加,這兒特別提拔年輕的人,所以我在這方面是吃虧了,只恨出來太晚。在我們國內是年老的人吃香,在此是年輕的人。我想回到台灣,也是因為我的藝術的根是生長在那兒,因為我想表現的是台灣那種鄉土味,遠離了它,我的藝術似乎就失去了滋養。」(註27)至此席德進已然清楚接下來他必須回到中國人的社會去,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他必須要承受來自四面八方的質疑及壓力,蔣勳就曾經為文談到席德進那時候徘徊在歸國與否的矛盾心情:「我想!這時的席德進真是很矛盾,一方面是西方的前衞和現代,在呼喚他內心任性恣情放肆的感官,另一方面,中國古老沉靜的傳統又似乎凝視著他,使他即使在縱情之餘,也感覺著一點中國子孫的責任吧!……『那時候回來真是要好大的勇氣啊!』他好像到今天還感覺到那時候的壓力。他說:『那時候,大家都覺得既然出去了,一定是在外面混不下去才回來。』是的,我們可以相信,1966年席德進回來前後,出國的畫家後來決定回來,如席德進一樣死心塌地待在台灣的人,真是寥寥無幾。」(註28)
我們從1966年3月14日席德進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這時候他內心的掙扎矛盾,已然達到了沸點:「我就是無時無刻不在矛盾中,我現在可以馬上動身回台的,只要把手續辦好,可是我不知為甚麼又不想動了,又在猶豫不決,又像捨不得離開這單純、自在、無顧慮的巴黎生活。我這一生,許多重大的變故,皆由於被動,如到台灣,出國等,這次,卻要我自己主動來支配我的命運,困難就在這兒了。但是我恐怕還是要下重大的決心,不顧一切而回來,因為我的理想是一定得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才能實現,我真希望有甚麼人逼迫我回去。」(註29)沒有誰能真的逼迫他回去,常玉失敗的故事只在無形間起了催化的作用,終究戰勝的是來自心底強烈的吶喊以及遠鄉的呼喚,他以堅定的口吻說:「我最近突然覺得巴黎對我已沒有多大的意義了!因為我不想再去看那些畫展了,看多了對我有妨礙,我需要生活於自己的土地上,感受自己人民的生活與情感,從那兒來創造我的藝術性,給畫的生命與泉源是在台灣,巴黎無法給我這些。」(註30)他相信隨著交通的發達,國與國之間的距離不斷縮小,即便他現在先回到台灣,將來如有需要,他還是隨時可以出國的,他自我安慰的說:「世界一天天在變,我們的觀念也應該變了,不能死守巴黎,巴黎已非廿年前的巴黎了,若認為繪畫一定非巴黎不可,這種觀念已落伍。其實巴黎已在沒落,這兒人對藝術的冷漠已令人心寒。有人說去美國呀!何必去湊熱鬧呢?我們中國是一大國,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文化、歷史,為甚麼要捨棄自己而不顧?去寄人籬下而企求虛名?厚利?我們不能逃避,我們應該為愛我們自己的國家而受苦,不該為自己的私利、小我而背離了國家,去求得一時的安然。」(註31)大概是懷才不遇的常玉最終潦倒巴黎的經驗給他以莫大的警惕,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他執意要回到中國人的國度,回到他熟悉的台灣,去開創更具有東方文化特質的繪畫藝術。他甚至自比為西方的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和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因遠離了巴黎而創作出更純真、更接近自然的感動人心之作:「許多人都不回國,因為他們『聰明』。但我的良知告訴我,我要回國,人家不作的傻事,我才要作,人家不需要祖國,而我需要她。她也許醜,但我們能怨恨母親醜嗎?她有許多缺點,但我們得原諒她,像寛恕母親一樣。我將來要用我的熱忱在台灣再生活、再創造,我要使台灣不朽。那兒的陽光,土地的氣息,人的精幹……凝固於我的畫上。像高更一樣,躱開了巴黎,而畫出了大溪地土人的原始誠樸。像梵谷一樣躱開巴黎,而畫出南方的陽光和向日葵的生命。」(註32)
別了巴黎 別了常玉
1966年3月31日席德進獨自踏上歸程,乘坐飛機離開巴黎,意外的是同鄉老畫家常玉專程趕到機場來為他送行,讓他備感温馨。他先飛赴意大利的羅馬、拿波利等地旅遊,再從希臘轉曼谷,約三週以後抵達香港,並在當地的上海商業銀行畫廊開了一次個展,6月9日正式飛回台灣,結束了長達四年的海外流浪。還在香港的時候他就先寫信向友人透露回歸東方的因由:「我這個流浪人是最適合漂泊的生活。現在剛好把地球繞了一圈,我覺得我是東方人,仍屬於東方,西方的好,抓不住我的心。我愛自己生長的國土,我愛中國人的生活,雖然這種生活是紊亂、窮困、髒,但這些就是它的性格、面貎;這些正可供我創造藝術的泉源與動力。我之所以拾棄了西方高度的文明生活、秩序的社會就在此了。」(註33)這番話可以為席德進毅然離開巴黎回歸台灣的抉擇,作出了最有力的解釋。等到飛機著陸在台北的那一刻,他更是難掩興奮之情:「那正是六月裡少見的雨季。飛機穿插在滿含水份的雲層中,偶爾露出一片浸了雨水的大地。我想辨識那些農村、道路與河流;一座橋出現,我立刻認出那是圓山中山大橋,而飛機已滑上了松山機場的跑道。旁邊綠色的田野,紅磚牆的農家,披著簑衣的農夫,這不是法國的景色,也不會是香港。這是台北——我要歸向的地方;一個我曾住過十年的城市,自己的國土。」 (註34)
回到台灣之後,席氏在1970年代全力投入發掘鄉土與大自然之美,把壓抑多時的思鄉情結亳無保留的傾注在作品之中,無心插柳的在國內掀起了一波排山倒海的鄉土文化浪潮,但他一直未曾忘懷當年在巴黎與常玉結交的點滴,以及他心裏頭想把常玉的故事寫出來的承諾,終於他所撰寫的〈一生沉沒在巴黎的中國老畫家常玉〉一文,發表在1971年5月號的《雄獅美術月刊》上,為國內首度出現專題介紹常玉的文章。常玉這個名字對於當時台灣的藝術愛好者而言是相對陌生的,透過席氏生動的文字敍述,讓讀者對這位旅法畫家有了初步的印象。席氏的文章,對一位在異鄉默默無聞,遽然驟逝的中國老畫家而言,著實起了關鍵的鈎沉作用,同時亦見證了兩人之間短暫卻真摯的珍貴情誼。
蝺蝺獨行 兩個漂泊的四川畫魂
和席德進相同,常玉晚期作品畫面充斥著一股濃得化不開的荒涼孤寂感。常玉本身的性格低調又孤僻,雖然旅居巴黎的日子不算短,朋友也有不少,但真正深交的卻並不多,據他的好友張易安小姐的回憶:「常玉在1950年代經常與一群歐洲藝術家們如莫諾利、馬賽.范.甸南、菲利.伊其利及阿拔圖.傑克梅第等人相處。張易安回憶,常玉的潦倒與孤僻不見容於當地華僑,他只有跟這些思想開放而大多比他年輕的歐洲朋友在一起時,較為輕鬆自在並找到慰藉。儘管如此,常玉跟他們之間的交往還是保留了相當程度的隱私,以致於他們對常玉的印象僅限於他的温和及幽默等,顯示出他們不是真正了解常玉。」(註35)席氏在巴黎的三年當中,想必有看過常玉那些晚期作品,潛移默化之下可能已受到對方的影響。席德進回想他在常玉巴黎的畫室中欣賞老畫家展示他的近作:「……他用極差的顏料,許多是用油漆代替的,都畫在木板上。大多是想像畫的。有幅大畫,整片原野裏只有一隻大象在奔跑,顯得既渺小,又孤獨,很有氣魄。」(註36)撇開技巧的問題不談,席德進與常玉兩人的晚期作品中一個最大的共通點,大概是二人在畫面上皆不約而同呈現出一種「獨立蒼茫天地間」的悵然吧!常玉晚年最喜歡在畫幅上營造出一個廣袤的空間背景,顏色通常很深沉,看起來像一片無垠的荒漠、有時又像一塊沙洲或草原、或是深不可測的海底,然後把要描寫的物象包括各式動物、樹木、枯枝等體積縮小至不成比例的地步,一種荒謬的孤寂感覺便油然而生,不管主題是獨自翱翔的沙漠飛鷹、回首長嘯的老虎、夜幕下翻滾的黑豹、悠游在深海中的魚兒、或在草原中奔馳的大象,全都顯得遺世而獨立,睥睨人世間的一切,這是否意味著畫家身為一個異鄉人,在巴黎闖蕩,卻始終懷才不遇、鬱鬱不得志的悲涼境遇?實在頗堪玩味。反觀席德進,他晚期水彩畫中最常描繪的景象,諸如溪畔的鴨羣、水田中的水牛、參天古樹下閒坐的孤獨老人、莊嚴肅穆的廟宇、或是被群山圍繞著的古舊房舍,在畫家的筆下,通通轉化成滄海中的一粟,似乎慨歎蒼生在大自然中的渺小和無奈,又像在哀悼世間美好事物的短促,而企圖要趕在消逝之前抓住那一份蒼涼的美感。他晚期的人像油畫,更出現如同常玉般以大筆刷染單色背景的效果,人在偌大的畫幅中顯得既渺小又卑微。而當他在捕捉台灣的景色諸如淡水、安平漁港、基隆港、南方澳或金山海岸時,畫中總反覆出現各式的漁船,他認為船通過人的創造被賦予了生命的形象,具有一種游移而飄逸的美。船-曾在風浪中顛簸、漂泊、追尋、迷失、掙扎、奮鬥……經歷無數風雨險阻,如今寧靜地靠岸,像化石般停泊在郁鬱的天幕下,向旅人們傳遞著一個無聲的信息,閃爍著它生命的光華,仿如畫家在藝術路途上的坎坷,因此成了他畫上一個特殊的圖騰。 (註37)它所傳達的,無論在精神及形式上都非常接近常玉的晚期作品。有感於兩人的漂泊生涯以及對藝術所抱持的執著,席氏過世以後,其好友郭沖石即曾在一篇懷念故舊的文章裏說:「當席德進十年前首度於《雄獅美術》上報導流落巴黎的老畫家——常玉其人其畫時,一股蒼茫的感覺縈繞我心頭,而那襲雖為生命折騰卻不願為藝術低頭的落寞身影,往往使我把席、常兩人的形象疊印、彼此不分。」 (註38)
遲來的桂冠
綜觀席德進從1948年來台至1981年病逝台北,這三十多年間的發展比起常玉在巴黎的落拓可謂順遂許多,畫作銷售情況一直是很不錯,加上為數眾多慕名而來委託繪製肖像的生意始終沒有斷過,過世時身邊累積了約五佰多萬元的銀行存款,臨終前交託好友為自己成立了基金會,並預先規劃好墓園的設計,其喪禮可謂備極哀榮。(註39)只是在他身後,他的高知名度對他畫作的行情不但沒有多大的提昇,卻倒像是沉睡了一般停滯不前。上天給席德進開了一個大玩笑,在他的畫藝正達到高峰的時候卻把他的生命收回,讓他無法繼續下去,他生前曾經短暫擁有過的榮耀和風光在他死後這二十多年間卻又慢慢的沉寂下來。常玉遲來的桂冠在蓋棺後足足等了快三十年,那麼席德進呢?到底還要多久世人才能重新體認其畫作的精髓,並還給他該有的地位呢?
悼我孤獨的弟兄們
隨著時間的腳步,當更多有關於常玉的生平事蹟被整理及報導出來,我們再回頭看席氏所寫的那篇〈一生沉沒在巴黎的中國老畫家常玉〉時,的確很難不為常玉及席德進這兩個同樣漂泊異鄉的畫魂而發出嘆喟!常玉為了能全身融入歐洲的畫壇,不惜放棄歸國發展;席德進則為了藝術而寧願接近鄉土,擁抱孤獨。還在巴黎的時候,有一個深秋的午後,席氏特意去拜謁了他一直奉為楷模的偉大畫家梵谷的墓,回來後寫下了一則感人肺腑的短文〈謁梵谷的墓〉:「我除了速寫本和照相機,甚麼也沒有帶。但我帶了滿腔的崇拜與熱忱,來拜謁我們的兄弟——梵谷之墓。恕我敢稱梵谷為我們的兄弟。假如我還配得上是屬於他那為追求生命、藝術的一群。不管怎樣,此刻我的整個身心,是在為這一位「親人」而顫動。我孤獨地一個人,從遙遠的東方來,我孤獨的心,想找到我們這位為孤獨而死的兄弟的影子。……為甚麼沒有人為梵谷置一個銅像?為甚麼沒有人在他墓碑上刻下偉大的讚詞?為甚麼沒有人為他修個大理石的墓地方?……梵谷早已為他自己樹立了銅像;但不是銅像,而是他堅定苦鬥的精神,對生命的追求。梵谷早己為他自己的墓碑,刻出了偉大的詞句,那便是畫上的色彩和線條。梵谷的墓地是美術館。我走出墳場,踏上歸途,殘陽照著山野,把大地染成一片傷心的紫色。教堂的黑影,傳出沉鬱的鐘聲。我直直地望著遙遠的天際,拖著我孤獨的身影。我突然高聲向天空中震喊:『呵!梵谷,你是我們的榜樣。』於是天際模糊,我熱淚盈眶。」(註40)
梵谷的愛情生活從來就不順遂,滿腔的創作熱忱又無法獲得世人的諒解,還好在生命的最後幾年移居至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當地的田園風光和赤熱陽光深深震懾著他,強大的創作慾望終於得到宣洩,不料因與畫友高更意見不合,割掉了自己的一個耳朵,而被迫接受精神疾病的治療。他一面飽受神經衰弱的折騰,卻仍堅持在戶外寫生作畫,只可惜終究敵不過現實的冷漠而提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身後遺留下八百多幅不朽的油畫作品,感動了無數蒼生,但他的墓碑卻是如此簡淡素樸。(註41)席德進晚年因罹患胰臟癌,不得不把部份受到腫瘤壓迫的膽管切除,為了使膽汁導流於體外,手術後必須在身上安裝一個用來盛載膽汁的瓶子,每天把苦稠的膽汁分三次喝回體內,真是苦不堪言!也許知道自己時日無多,雖然萬般的不甘心,行動也非常不便,卻越是要把握時間,強撐起精神,繼續開著他的紅色小車作環台寫生,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們兩人對鄉土的熱愛以及對創作的激情是非常接近的。常玉孤身在巴黎畫壇闖蕩,最終因瓦斯中毒而魂歸天國,死後被埋骨荒塚,無人聞問。筆者以為,席德進對素昧平生的偶像梵谷,猶能以「兄弟」相稱,又親往拜謁他的墓地,假若他有生之年,得知常玉身後的淒涼境況,想必也期盼能重回巴黎,前來這位跟他相知相惜的同鄉前輩的墳前燃一炷香,甚或一掬同情之淚吧!
(本文作者為台灣蘇富比創始團隊專家、常玉油畫全集譯者之一、廣達文教基金會藝術顧問)
註1 李明明,〈三零年代的巴黎畫派與中國畫家常玉、潘玉良〉,《美好年代——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收藏展》,(台北:時藝多媒體傳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1月),頁26-35。
註2 見席德進撰,〈一生沉沒在巴黎的中國老畫家常玉〉,《雄獅美術月刊》,(台北:1971年5月號),頁18-22。
註3 龐薰琹,《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8年),頁85。
註4 同前註2。
註5 同上。
註6 同上。
註7 同上。
註8 同上。
註9 同上。
註10 有關勒維夫婦與常玉之間的交往,詳見衣淑凡,《常玉:油畫全集》,(台北:國巨基金會,大未來藝術出版社,2001年),頁82-85。
註11 同前註2。
註12 同上。
註13 同上。
註14 席德進,《席德進書簡——致莊佳村》,(台北:聯經文學出版社,1982年7月),頁63-65,1964年6月20日。
註15 同前註2。
註16 同前註14,頁54-56,1964年4月16日。
註17 同上。
註18 《羅勃.法蘭克之常玉》蘇富比拍賣目錄,(台北:1977年10月19日)。
註19 同前註2。
註20 同前註14,頁49-50,1964年3月9日。
註21 同前註14,頁39-40,1963年12月19日。
註22 同前註14,頁61-62,1964年5月10日。
註23 見席德進撰,〈一生沉沒在巴黎的中國老畫家常玉〉,《雄獅美術月刊》,(台北:1971年5月號),頁18-22。
註24 同前註14,頁90-92,1965年1月12日。
註25 同上。
註26 同前註14,頁105-106,1965年6月28日。
註27 同上。
註28 蔣勳,〈生命的苦汁——為祝福席德進早日康復而作〉,《雄獅美術月刊》第一二四期,(台北:雄獅美術月刊社,1981年6月號),頁26-37。
註29 同前註14,頁144-145,1966年3月14日。
註30 同前註14,頁134-135,1966年1月3日。
註31 同上。
註32 同上。
註33 同前註14,頁150-151,1966年4月21日。
註34 席德進,〈回到了台北〉,《皇冠雜誌》第151期,(台北:皇冠雜誌社,1966年9月),頁56-59。
註35 衣淑凡,《常玉:油畫全集》,(台北:國巨基金會,大未來藝術出版社,2001年),頁74。
註36 同前註23。
註37 《繁華落盡見純真—席德進世紀再現特展》圖錄,(台北:民生報社,2001年1月),頁102。
註38 郭沖石,〈無限延伸的水平線〉,《懷思席德進》,(台北:懷思席德進委員會編,1981年8月12日),頁54-62。
註39 見中國時報1981年8月3日〈我真是不甘心啊!〉一文,《懷思席德進》,(台北:席德進懷思委員會,1981年8月12日),頁104-105。
註40 席德進,〈謁梵谷的墓〉,《席德進的回聲》,(台北:大林文庫48,1970年3月15日),頁79-82。
註41 有關梵谷的生平,坊間著作甚多,筆者推薦Irving Stone原著Lust for Life,余光中譯《梵谷傳》,(台北:大地出版社,197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