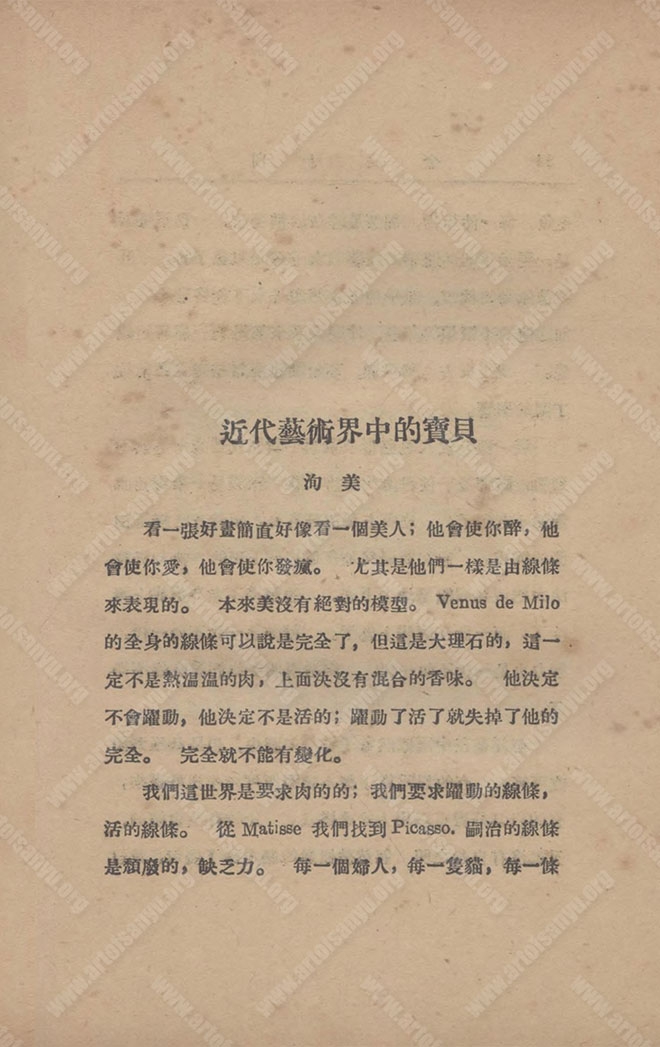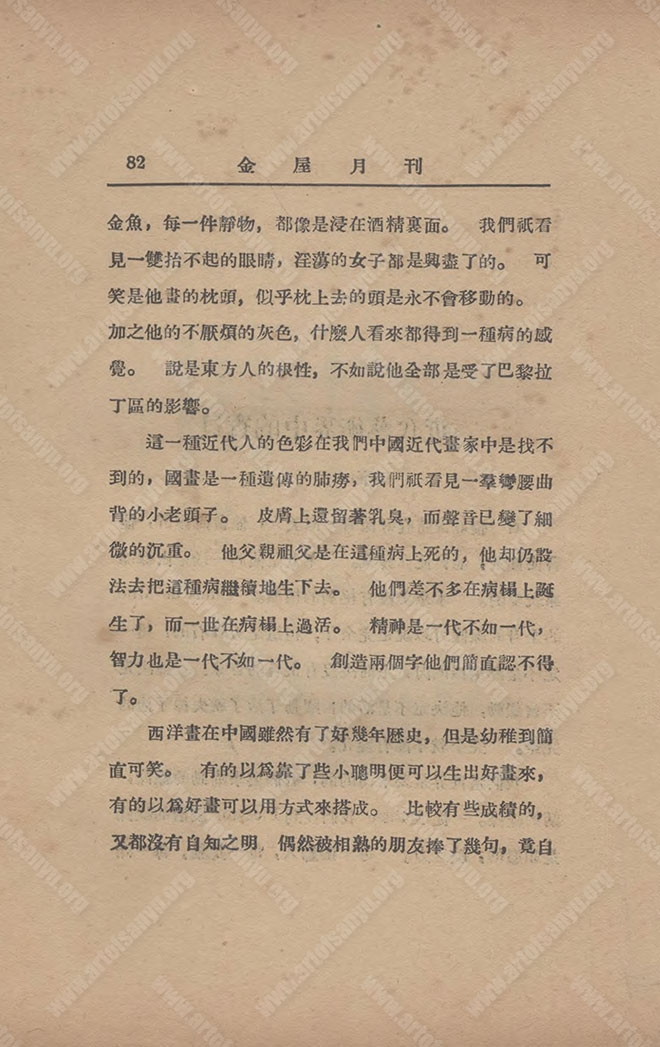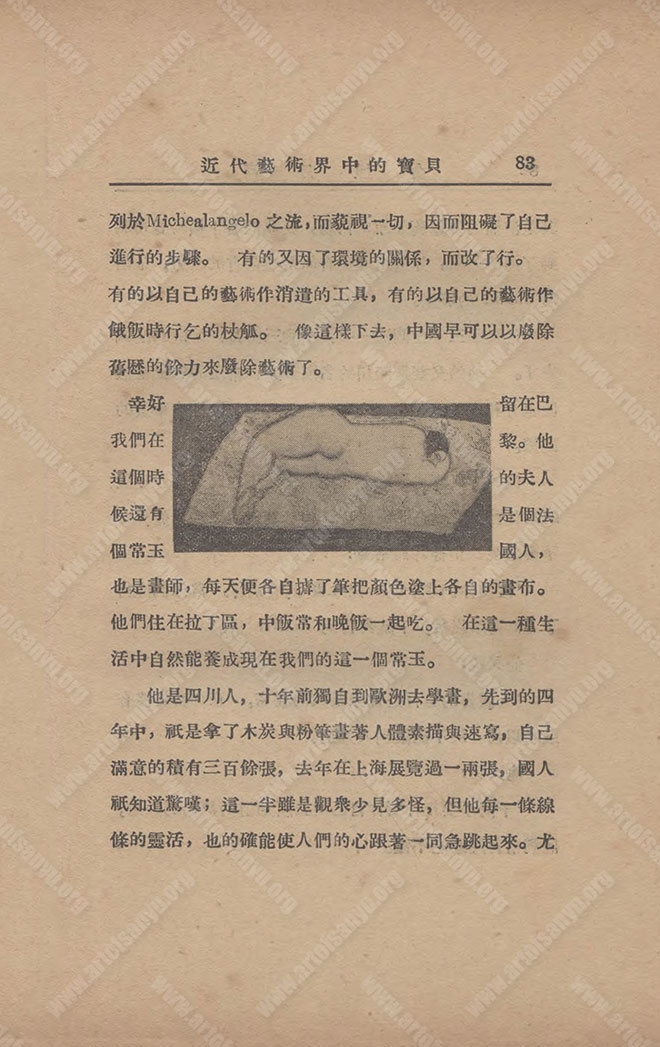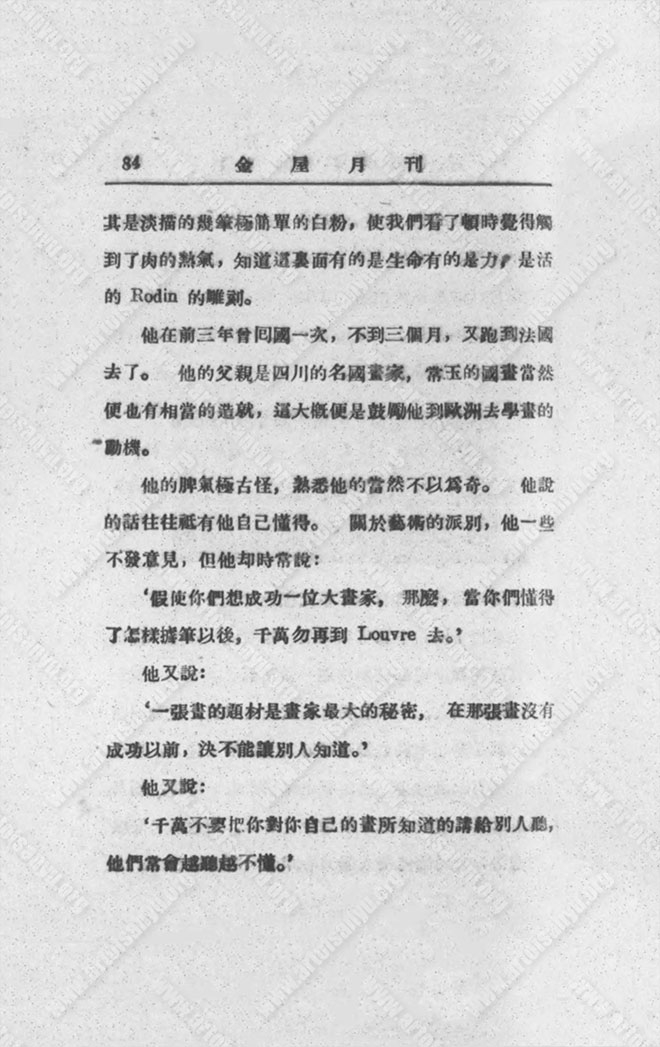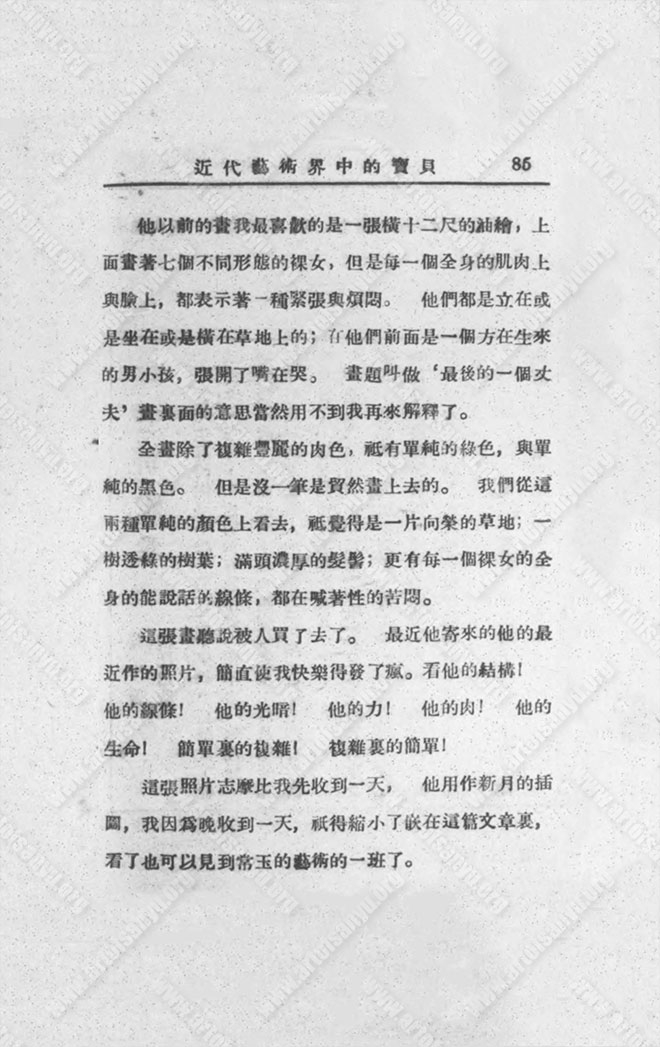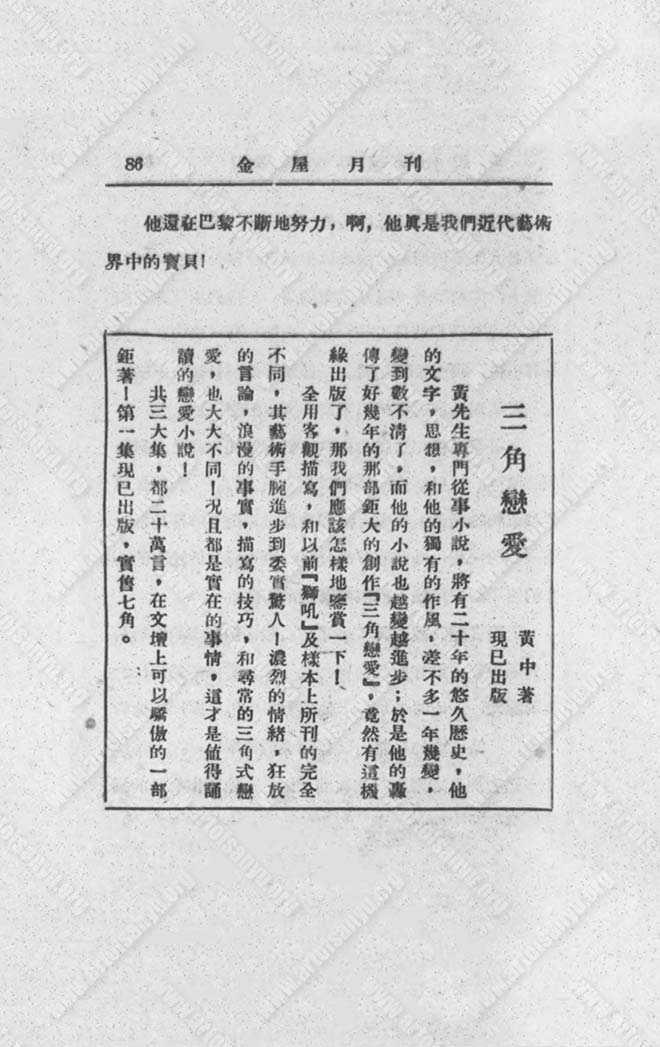看一張好畫簡直好像看一個美人;他會使你醉,他會使你愛,他會使你發瘋。尤其是他們一樣是由線條來表現的。本來美沒有絕對的模型。Venus de Milo的全身的線條可以說是完全了,但這是大理石的,這一定不是溫熱熱的肉,上面決沒有混合的香味。他決定不會躍動,他決定不是活的;躍動了活了就失掉了他的完全。完全就不能有變化。
我們這世界是要求肉的;我們要求躍動的線條,活的線條。從Matisse我們找到Picasso,嗣治的線條是頹廢的,缺乏力。每一個婦人,每一隻貓,每一條金魚,每一件靜物,都像是浸在酒精裡面。我們祇看見一雙抬不起的眼睛,淫蕩的女子都是興盡了的。可笑是他畫的枕頭,似乎枕上去的頭是永不會移動的。加之他的不厭煩的灰色,什麼人看來都得到一種病的感覺。說是東方人的根性,不如說他全部是受了巴黎拉丁區的影響。
這一種近代人的色彩在我們中國近代畫家中是找不到的,國畫是一種遺傳的肺癆,我們只看見一群彎腰曲背的小老頭子。皮膚上還留著乳臭,而聲音已變了細微的沈重。他父親祖父是在這種病上死的,他卻仍設法去把這種病繼續地生下去。他們差不多在病榻上誕生了,而一世在病榻上過活。精神是一代不如一代,智力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創造兩個字他們簡直認不得了。
西洋畫在中國雖然有了好幾年歷史,但是幼稚到簡直可笑。有的以為靠了些小聰明便可以生出好畫來,有的以為好畫可以用方式來搭成。比較有些成績的,又都沒有自知之明,偶然被相熟的朋友捧了幾句,竟自列於Michealangelo之流,而藐視一切,因而阻礙了自己進行的步驟。有的又因了環境的關係,而改了行。有的以自己的藝術作消遣的工具,有的以自己的藝術作餓飯時行乞的杖觚。像這樣下去,中國早可以以廢除舊曆的餘力來廢除藝術了。
幸好我們在這個時候還有個常玉留在巴黎。他的夫人是個法國人,也是畫師,每天便各自捏了筆把顏色塗上各自的畫布。他們住在拉丁區,中飯常和晚飯一起吃。在這一種生活中自然能養成現在我們的這一個常玉。
他是四川人,十年前獨自到歐洲去學畫,先到的四年中,只是拿了木炭與粉筆畫著人體素描與速寫,自己滿意的積有三百餘張,去年在上海展覽過一兩張,國人只知道驚嘆;這一半雖是觀眾少見多怪,但他每一條線條的靈活,也的確能使人們的心跟著一同急跳了起來。尤其是淡描的幾筆極簡單的白粉,使我們看了頓時覺得觸到了肉的熱氣,知道這裡面有的是生命,有的是力,是活的Rodin的雕刻。
他在前三年曾回國一次,不到三個月,又跑到法國去了。他的父親是四川的名國畫家,常玉的國畫當然便也有相當的造就,這大概便是鼓勵他到歐洲去學畫的動機。
他的脾氣極古怪,熟悉他的當然不以為奇。他說的話往往只有他自己懂得。關於藝術的派別,他一些不發意見,但他卻時常說:「假使你們想成功一位大畫家,那麼,當你們懂得了怎樣捏筆以後,千萬勿再到Louvre去。」
他又說:「一張畫的題材是畫家最大的秘密,在那張畫沒有成功以前,決不能讓別人知道。」
他又說:「千萬不要把你對你自己的畫所知道的講給別人聽,他們常會越聽越不懂。」
他以前的畫我最喜歡的是一張橫十二尺的油繪,上面畫著七個不同型態的裸女,但是每一個全身的肌肉上與臉上,都表示著一種緊張與煩悶。他們都是立在或是坐在或是橫在草地上的;在他們前面是一個方在生來的男小孩,張開了嘴在哭。畫題叫做《最後的一個丈夫》,畫裡面的意思當然用不到我再來解釋了。
全畫除了複雜華麗的肉色,只有單純的綠色,與單純的黑色。但是沒一筆是貿然畫上去的。我們從這兩種單純的顏色上看去,只覺得是一片向榮的草地;一樹透綠的樹葉;滿頭濃厚的髮髻;更有每一個裸女的全身的能說話的線條,都在喊著性的苦悶。
這張畫聽說被人買了去了。最近他寄來的他的最近作的照片,簡直使我快樂得發了瘋。看他的結構!他的線條!他的光暗!他的力!他的肉!他的生命!簡單裡的複雜!複雜裡的簡單!
這張照片志摩比我先收到一天,他用作《新月》的插圖。我因為晚收到一天,只得縮小了嵌在這篇文章裡,看了也可以見到常玉的藝術的一斑了。
他還在巴黎不斷地努力,啊,他真是我們近代藝術界中的寶貝!